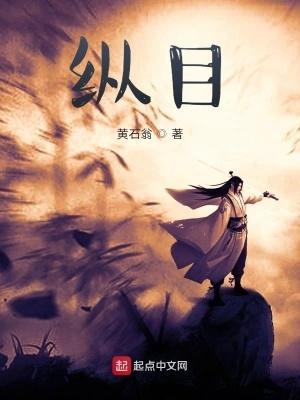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非遗我传承 > 第十三章 成功的重量(第1页)
第十三章 成功的重量(第1页)
当个作者玩玩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初步成功的兴奋感,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在胸腔里荡漾了一整晚。第二天清晨,陆知简几乎是迎着第一缕晨光就醒了过来,睡意全无。他迫不及待地来到工作室,再次检查了那些模拟数据和涂刷了自制颜料的测试样本。
一切稳定。
窗外的麻雀在叽喳叫着,远处传来早班公交的报站声,寻常的都市清晨,此刻在他听来却格外悦耳。他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指尖悬在苏槿的微信头像上,那句“成功了”几乎要脱口而出。
可就在按下发送的前一秒,他停住了。
一种奇怪的情绪攫住了他。这成功,不仅仅是系统提示里冷冰冰的“稳定性提升”,也不仅仅是笔记本上新增的一行有效数据。这里面,有陈老爷子缓慢沙哑的叙述,有苏槿在材料市场递来的那瓶水,有他自己无数次熬胶失败的焦糊味,有那包来自城中村灶底的、带着烟火气的灰烬……这份成功,沉甸甸的,带着温度,带着属于他一个人的、笨拙而执拗的探索痕迹。
他忽然有点……舍不得立刻分享出去。
这种情绪对他而言很陌生。他向来习惯用数据和结果说话,成功就是成功,失败就是失败,分享是为了获取反馈或确认。可这一次,他只想把这份混杂着多种滋味的初步成果,在自己心里多捂一会儿,像藏着一颗刚刚孵化、还带着体温的蛋。
他默默退出微信,将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细致地规划下一步——如何将这套方法安全地应用到真正的年画上。风险依然巨大,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失误,都可能毁掉那脆弱的原稿。他需要更周密的方案,更多的局部测试。
接下来的两天,陆知简彻底进入了“闭关”状态。他谢绝了所有不必要的打扰,连首播都发了公告暂停几天。工作室里,各种试剂、纸张、显微镜和记录本铺得到处都是。他反复调整着颜料配比,在不同酸碱度、不同湿度的环境下测试固化效果,用【微痕读取】技能观察颜料与纸张纤维结合的微观状态,试图将那个“土方”的效力发挥到极致,同时将风险降到最低。
他完全沉浸在技术的迷宫里,忘记了时间,也暂时将那个未拨出的电话抛在了脑后。
首到这天傍晚,他正对着显微镜观察一个关键样本时,放在一旁的手机不合时宜地、持续地震动起来。
思路被打断,陆知简有些不悦地皱了皱眉,目光并未离开目镜,只是伸手摸索着拿过手机,瞥了一眼来电显示——是“聚古斋”的钱经理。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语气带着一丝被打扰后的疏淡:“钱经理,你好。”
“陆先生!哎呀,可算联系上您了!”电话那头,钱经理的声音带着显而易见的急切,甚至有点夸张,“您这边……关于那年画的修复方案,有什么进展了吗?我们这边……唉,有点等米下锅啊!”
陆知简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不太喜欢这种催逼的态度,尤其是对待这种精细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修复工作。
“钱经理,修复方案还在研究和测试阶段,目前没有确切的结论。”他语气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距离感,“这类民间颜料的稳定性问题很复杂,我需要时间确保方案安全有效。如果贵馆觉得时间紧迫,或许可以考虑其他途径。”
这话说得客气,但意思明确:要么等,要么另请高明。
钱经理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语气立刻软了下来,带着赔笑:“哎哟,陆先生您别误会!我们肯定是相信您的!等,我们等得起!只是……只是馆里最近情况有些特殊,我这边压力也比较大……您多费心,多费心!”
又寒暄了几句,钱经理才悻悻地挂了电话。
放下手机,工作室里恢复了安静,但陆知简的心情却无法立刻平静下来。钱经理过于急切的态度,让他心里升起一丝疑虑。这批年画虽然有一定民俗价值,但并非什么绝世珍品,值得如此焦灼地催促吗?还是说,“聚古斋”或者这批年画本身,有什么他不知道的隐情?
他摇了摇头,暂时将这些杂念甩开。当务之急,是攻克技术难关。他重新将目光投向显微镜下的世界,那里有更清晰的线条和更确定的逻辑。
只是,经过这个电话,那份独自珍藏成功的微妙心情,似乎也淡去了些许。现实的、带着各种目的和算计的世界,终究会不断敲打他工作室这扇看似隔绝的门。
他看了一眼依旧安静的手机,苏槿的头像没有任何新消息提示。她似乎也很默契地没有来打扰他的“闭关”。
这样也好。他心想,重新埋首于他的实验数据中。有些重量,或许本就该独自承担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