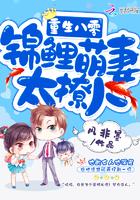奇书网>苏东坡传全三册 > 五 该复出了(第2页)
五 该复出了(第2页)
就在神宗那个“一年看重,两年起用,三年执政”的计划执行到一半儿、旧臣将起未起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谣言,说苏轼、曾巩两大才子一在黄州一在江宁,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了!至于为什么有此巧合?也有个解释:苏、曾二人文的章天下无双,却不能被当今皇帝重用。玉皇大帝爱这两人之才,就命二人驾鹤升天,到凌霄殿上做“翰林学士”去了……
这个吓人的传说一半是真的,文章和苏轼齐名的大才子曾巩确实在元丰六年病故了。另一半则是假的,苏轼仍然健在。之所以被人传为“身死”,是因为东坡居士病了半年,这半年里无诗、无词、无赋,连人影也看不见。天下人以前每月都能读到苏夫子的新词,忽然半年不见此公,就传出“仙逝”的谣言来了。
曾巩病死,神宗皇帝倒不怎么在乎。可苏子瞻是出了名的“旧臣首脑智囊”,如今皇帝正要重用旧臣,第一批提拔的人里就有苏轼,他却死了!这还得了?急忙叫人来问。然而黄州太远,苏轼又是被贬的官员,是死是活朝廷里的人闹不清,只能对皇帝说:“大约有此事。”
一听这话神宗又失望又伤感,连说:“可惜,可惜。”当天竟不用膳。后来才想起来,此事应该查问清楚才好。正好淮南转运使蔡承禧回京述职,即将回治所,神宗就命蔡承禧到黄州看一眼苏子瞻。
蔡承禧是苏轼的同年,也是好朋友,听说苏轼病死也很惊讶,急忙起程赶往黄州来。路过许州又去拜访了住在此处的范镇。
范镇当年担任翰林学士,因为反对王安石被贬了个七零八落,今年这位老臣已经七十五岁,到了风烛之年。听蔡承禧说苏轼病死,老头儿当场痛哭失声,蔡承禧忙说“未必真死”,范镇这才止住眼泪。立刻拿了几十贯钱给蔡承禧,告诉他:若苏轼真的去世了,这钱就是赙仪;若苏轼没事,就把这些钱送给他贴补家用。
说实话,来黄州这一路上蔡承禧也是提心吊胆,现在亲眼看见苏轼扶杖而出,虽然瘦弱些,总归还活着,这才松了口气。笑呵呵地说:“子瞻无恙事情就好办了。”
听蔡承禧话里有音,苏轼忙问:“朝廷有什么事?”
蔡承禧故作神秘地把嘴凑到苏轼耳边,压低声音:“陛下对朝局有了新的看法,那帮奸贼已经站不住脚,不但司马光、范纯仁即将回朝,子瞻不日也将复出。”
要是参寥和尚没来黄州,今天听了蔡承禧这些话苏东坡不知会怎样欢呼雀跃!可参寥和尚讲了一回禅,东坡居士已经看破了:世事纷繁都是梦幻,什么“奸邪”、什么“复出”都是虚妄,“也无风雨也无晴”才是境界。听了蔡承禧的竟不接口,脸上也没露出多少喜色。
蔡承禧是个官僚,一辈子见惯了城府如海的政客,对苏轼这种心里有事全写在脸上的老实人反而吃不透。见苏轼反应冷淡,以为此公久经历练,莫测高深,对朝局早就成竹在胸,自己多话徒惹人嫌,急忙换个话题:“子瞻在黄州几年着实受了不少苦,我看你这住处也不能将就,需要另起庐舍才好。”
蔡承禧这是要巴结苏子瞻。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大实话。参寥、巢谷、潘丙、古耕道、徐大受他们才是苏夫子的好朋友,蔡承禧一见苏轼就要送给他一套好房子,可放在“良心秤”上称一下儿,蔡承禧送的这套房子还没有参寥和尚的一首诗份量重。
“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孰轻孰重轻重苏夫子心里明白。再说,苏轼对自家盖的这座“雪堂”十分满意,笑问:“我这房子高大阔朗,有何不妥?”
蔡承禧指着雪堂的茅草屋顶:“漏雨不漏?”
“大雨时漏一些。”
东坡居士爱开玩笑,但不会说谎话。一听这话蔡承禧顿时急了:“漏雨的房子如何能住?盖房的事你别管了,一切有我!”见苏轼还要推辞,又说,“如今已是深秋,再不把房子盖好,几场雪下来你这‘雪堂’就是‘冰窖’!你自己不在乎就算了,难道连妻儿也不管?”
蔡承禧这话说得对。黄州地方潮湿,冬天阴冷刺骨,朝云身子弱,最怕冷,干儿又小,难道真让这“连心肉”一样的宝贝儿子在“冰窖”里过冬吗?
为了妻儿,苏轼真就不能推辞了。
蔡承禧在黄州并未久住,但他办事极快,备料雇工,很快就在雪堂边上盖起三间砖房,一间会客,一间读书,一间做寝室。因为房屋坐北向南,姑且称其为“南堂”。
苏轼的脾气像小孩子一样,见了新屋急忙要住,也不管屋里湿气未退,一家三口早早搬了过来。果然还是砖房好,下雨不漏冷风不侵,一家子得了庇护,连苏轼一直没断的咳嗽也忽然轻了许多。这时苏学士才想起来:原来自己黄州四年真的是在“吃苦”……
“无常是苦,然苦中有一点乐,衔而游之,当见活水。”这是早年东坡居士未得志的时候,京师兴国寺德香大和尚告诉他的话。那时候苏轼年轻,对禅理佛法一窍不通,现在他渐渐懂了,原来一个人不管怎么活着,他的人生总是“苦”的——就算当了皇帝照样苦不堪言。然而再苦的人生也有一点“乐”,找到这个乐趣就是源头活水,能带人出离苦海。
苏轼刚到黄州觉得很苦,后来渐渐不以为苦,越活越“甜”,后边这两年竟入了神仙境界。这是他无意中参透了“一点乐”,找到了生命中的“活水”。有意思的是,若问苏子瞻:什么是一点乐?什么是活水?他未必说得清楚。
这就叫知难行易。
蔡承禧走后苏轼又在“南堂”养了半个月,身体已经大好,依着他的脾气顿时闲不住了,回头一想,自己这一病,和黄州知府徐大受足有半年没见了。
苏轼刚到黄州,徐大受对他就那么关照,给了他那么多帮助,至于提浆到访、赤壁夜游,这份交情更不用说了。可苏轼除了到黄州第一年常赴酒宴之外,后头三年没怎么到知府那里拜访过,每次总是知府大人来拜访他。如今一病半年,想想,和徐知府快十个月没见了,也真想他,就把刚酿的好酒装了一壶,提着新酒来访故人。
苏轼过来的时候已到中午,徐府大门紧闭,门前车马绝迹十分冷清。苏轼也没多想,上前叩门,好半天,大门开了一条缝儿,一个老头子探身出来:“啥事?”
苏轼忙说:“我是知府旧友,请通报一声,就说苏子瞻来拜。”
老头儿满脸诧异,把苏轼看了半天:“你是来吊丧的?怎么这时才来?”
老仆这话把苏轼吓了一跳:“什么吊丧?”
“徐知府早就过世了,你不知道?”
一听这话苏轼吓得脸色都变了:“太尊何时仙游?我没听说!”
见苏轼惊成这样,老头儿只得说:“徐知府一个月前就病死了,当时阖府吊唁,来行礼的人很多,你既是知府的朋友怎么没得信呢?丧事办完太尊家眷就扶灵回天台老家去了,新府尊还没到任,现在这院里空着没人住。”也不和苏轼多说,回身进去把门插上了。
想不到黄州知府徐大受已经故去了,苏学士惊痛交集,想起刚起黄州时徐太守对他的庇护,给他的帮助,如今故人已逝,自己连个信儿也没得着,吊唁都没来,越想越难过。徐家人都已迁去,满腹哀思无从寄托,只得从旁边一间木器铺里借了笔墨,在太守旧居外墙上写了一首诗:
“一舸南游遂不归,清江赤壁照人悲。
请看行路无从涕,尽是当年不忍欺。
雪后独来栽柳处,竹间行复采茶时。
山城散尽樽前客,旧恨新愁只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