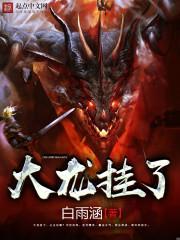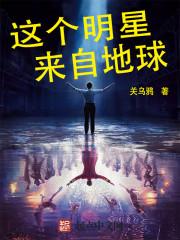奇书网>平民史诗的作者是谁 > 太阳纵队传说(第2页)
太阳纵队传说(第2页)
一九六三年进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有个诗社“蒲剑”——借屈原故事命名,是文怀沙先生所题。前任社长是范曾,我和白汝博接班。在“蒲剑”朗诵会上,范曾吟唱了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团委书记赵更生认为范曾是复古,皱皱眉头,要我朗诵现代的。我只能照念老马。老赵更皱起眉头。
我出来,在走廊见到范曾,俩人握手大笑。我们都不是当局的好孩子。
六
“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筱庄楼。参加的人有:张文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其目的无非是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我们打算每月搞一次沙龙,墙上挂画,朗诵作品,形成强力集团,打入社会。
那个阶段我写了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然而,不几天后,组织自行解散。
郭士英(那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他们的沙龙要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凛冽冬风百草散,我们立刻停止了组织活动,化整为零。
七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地下艺术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画家袁运生的毕业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美术》杂志登了这张画,学校里剑拔弩张。这张巨幅油画被搬出藏画楼,堆在乒乓球室,准备批判。
袁运生、丁绍生、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儿们。当时袁运生已去了吉林,还不知道要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于植信、蒋定粤分别商量,怎么救哥们儿一把。我忽发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没法批判。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
我决定独立行动。趁团员大会校园没人,我潜入体育馆,从画框下割下那张画,卷成一卷,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我家客厅的地板,吴尔鹿跑来欣赏。我大汗淋漓,一面为老袁高兴,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冲到美院,作为政治案件处理,气氛紧张。
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对我的邪大胆佩服得五体投地。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当局一旦知道,这一条就能判你。
我七个不吝,八个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八
聚会越来越隐密,而人员也在变更之中。
那时跟我最铁的是巫鸿。我们都来自101中,现在同班。志趣相投,又同时爱上蒋家的女孩子,我追蒋定粤,他追蒋定穗。蒋定粤的哥哥蒋之翘写古诗。他们家成了这一阶段的沙龙。
另一沙龙在周七月家。我们自幼是好友。他家有西方最新的唱片。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的唱片。他爹进来,脸色不好看,我居然没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应顺势放一张古典的,我却又放上了另一面。老天,我真是个祸头子。
老两口找我谈话,亮出了黄牌。当时觉得他们多虑,现在回想,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九
郭士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牟敦白,最早放出来,就跑来找我。他家成了另一个沙龙,其中有: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后来又见了郭路生。我们经常聚会,玩秘密的写诗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常常是咸菜。
有一次,董沙贝带了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了削,大家觉得特别有味。张士彦是老大哥,已经有工作了,每次来看我们,总是带一瓶“中国红”,大家齐齐喝彩。
十
我也试着给《人民文学》投过稿,由于主编因政治原因下台,没有成功。
我们决定自己出版手抄杂志,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我父母也参加了。其中有耿军、邬枫、蒋定粤、张大伟、张寥寥等。我主编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也许,那是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一九六六年,因为袁运生的画、“太阳纵队”、秘密聚会、法国留学生们、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公安局开始要逮捕我,我开始逃跑……在和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王东白的本子扉页我写下:相信未来。
最终,我被抓了回来。先在学校,后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无数次审讯,一再地追问那个“反动组织”——“太阳纵队”。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或许早已焚为灰烬。
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
十一
据说,有人已经开始研究这一段地下文化史;有人在着手收集、汇编那时残存下来的作品。
到底有没有“太阳纵队”那样一个地下文学组织?那的确是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