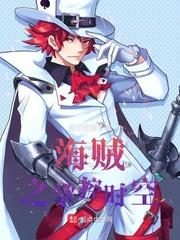奇书网>郁金香花开的雨夜简介 > 审讯之前(第1页)
审讯之前(第1页)
审讯之前
前不久,我停笔不再写小说了。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写小说,现在我对这件事已经不感兴趣了。生命中还有其他的事可做。要是继续写下去,我不过是在重复自己而已——我开始意识到,这些念头不请自来,出乎我的意料,它们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不去,折磨着我,并且一天天变得愈加强烈,让写小说的冲动显得愈加单薄。一开始,我还能借着惯性写一写,后来惯性也不够用了,于是我就干脆放弃了。
这样的变化发生在我身上,有点奇怪。这种状态并不常见。起初,我有些困惑,每天晃晃悠悠地打发日子。我把很久没读的书拿出来读。我去散步。与其说是散步,倒不如说是一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一边努力让自己不要忘记暖气炉的过滤板该换了。每周二和周四上午,我跟妻子一起去一家公共泳池游泳。我们差不多每周去看一次电影,每周去咖啡馆吃两次午餐。我的人生显然已经步入庸俗的退休状态。绝大多数时候,我就在家打扫卫生,整理屋子,把该修的地方修一修,该翻新的翻翻新,于是时间一周一周过去,我一点小说也没写。有些时候,我会沮丧地发现一晃就到了中午,可是这种不安从一开始就并不强烈,顶多也就是突然来一下子,要么就是一种短暂的空虚感。持续更久的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有点不太对劲。后来,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直到我每天早晨醒来,压根儿不会再想起写小说这件事,也不会再惦记它。我已经彻底把写小说的事抛在脑后了。如今,人生又有了其他可能。如果这些文字让你对眼前的这本书产生了好奇——好奇我是不是在开玩笑,或者在卖关子,抑或是漫游进入了元小说(1)的边界,或者干脆这篇小说就是自动生成的——那么,我想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
10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摘了四排树莓藤上的果子。那些果子上原本还带着叶子,但是在我边挑边摘的过程中,叶子落了一些。等我忙完这些,父亲打电话来了。他说,有两件事:一是他后院的一棵树倒了,二是他出了个小小的交通事故。倒下的那棵树虽然恼人,但是拖一拖也无所谓。但是那个交通事故就有点麻烦了,因为他的车没法开了,而他每天早上还得去上班。
“没,”他说,“我没受伤。没有人受伤。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不好的一面,我是过失方。我知道。我没法怪别人。我撞到了一辆停着的车。我拐了个弯,结果撞到人家了,于是我就坐在那儿想:‘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的人生开始结束了。’”
“你妈妈,”父亲接着说,“曾经在停车场发生过一连串的剐蹭事故,然后又有一次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结果就是,她已经差不多两年没摸过方向盘了,当然,这些你都知道,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只有这一辆车,可是呢,这辆车现在没法开了。不过,大体上说,我们都好好的。”
我父母的确都好好的——大体上说。他们依然住在我和姐姐从小长大的那幢房子里——是一座砖墙的盐盒式房子,窗台也是砖头砌的。门外的水泥台阶已经裂了口子,台阶一侧有铁栏杆。房子里所有的窗户都不太好关,所有的窗玻璃也都彻底磨花了。窗户外面的灌木丛因为经常不按时修剪,会从窗户缝里戳进来。有一间半地下室,里面塞满了留着“以后”用的东西,然而这个“以后”从来就没发生过。屋顶烟囱的地方有些漏雨。房间的天花板很低,门厅都用薄薄的板子包着。光线随意地照在家里的每一件物品上——从茶几上的陶瓷塑像,到那堆攒下来的火柴盒,还有餐具柜里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瓷器。我那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已经把厨房餐厅合二为一的区域作为自己发挥余热的舞台,把那里简单装饰了一番:安了一排卡座,外加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把空间填得满满的。想要从吃饭的餐桌旁边绕过去,进到他们在一扇窗户底下给自己做的“鸟窝”里面,还是需要一点功力的——按照我父亲的解释,此时此刻,倒下的那棵树的树枝正好杵在那扇窗户上,枝丫都蜷在一起。
我去了一趟。这对我来说不难。我住的地方离他们大概十五分钟车程,这一点,你可以认为是件令人沮丧的事——几乎一辈子都待在从小长大的地方。不过,我倒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事实上,我觉得挺好。况且,要是确实有理由需要搬家,比方说因为工作,或是我妻子想搬,我会搬的。我姐姐也没挪过地方。她也住在西雅图,而且她不止一次说过:“干吗要搬啊?”
我父母家后院里倒下的是一棵云杉,是被最近的一场暴风刮倒的。树干从顶部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折断,那些枝丫现在要么戳进泥里,要么朝天上竖着,好像硬硬的胡楂儿。树皮、针叶还有球果在院子里落了一地,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树脂味。我用一把油锯清理战场,直到院子里恢复了应有的整洁。接着,我便和父亲一起猫着腰钻进车库后侧角落里那个用雪松木搭成的棚子,去看他的车。车库已经摇摇欲坠,快散架了,旁边是一段满是腐叶的天沟。车的前排驾驶座那里被撞扁了,其中一盏前灯摇摇晃晃地耷拉着。“是这样的,”他说,“等我开到家——撞车的地方离这儿只有两个街区——冷却箱里的水全流出来了。所以现在只能停在这儿,得等我把原因找出来才行。”
* * *
第二天早上,7点半,我去接父亲上班时,他已经穿戴整齐,站在门廊里等着了。他一手抓着长度到脚的雨衣,另一只手拎着一个买菜用的塑料袋,坐进我的车里,似乎满心期待的样子。我感觉。
我们出发了。我闻到了Vitalis发胶的香味。父亲戴了一条卡夹式领带,穿着背带裤,外面套了一件单排扣的夹克。他多少年都是这身打扮,或是跟这差不多的搭配,以前看着还是挺精神的。可是现在,这身衣服在他身上却显得特别大,好像借来的一样。像他这样身材精瘦的老头容易让人觉得讨厌,尤其要是再配上皱着眉头的表情,就更不招人喜欢了。要是在一群年轻人里,那样的人连呼吸都仿佛散发着对生命以及对死亡的憎恶。不过,父亲不是那样的。他没有那种凶巴巴、冷冰冰的感觉。他的眼神依旧灵动,跟你说话的时候,脸上总带着笑。他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热情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到了市中心,我把车开进他办公室楼下的车库里。“你要不要上来坐坐?”他问,“还是直接去图书馆?”
前一天,我为了让他确信开车送他上班不会给我添麻烦,就跟他说我要去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当然,我是骗他的。)可是,这会儿才七点四十五,图书馆十点才开门。于是我跟他说,还没到时间。
我们下了车。父亲把雨衣搭在一边胳膊上,另一只胳膊上挂着塑料袋,在车库光秃秃的灯泡下面大踏步地往前走,好像迟到了似的。他伸手冲车库收费亭里的工作人员示意,跟人家打招呼,那人也冲他竖起拇指,作为回应。
我们乘扶梯上了两层,又进电梯坐到二十七层。他的律所就在那里。父亲把大门的锁打开,又把长长的一排灯都啪啪摁亮,然后就到前台后面查备忘录(显然,他的律所仍然允许用纸笔记录),想看看有没有他的事。没有。所里静悄悄的。
我们去了他的办公室。我已经很久没去过了。父亲把雨衣放在一张椅子上,又从他一路拎着的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小一号的塑料袋,里面装了满满的麸皮麦片,还有一份《西雅图时报》。接着,他拉开一个装满纸碟和塑料勺子的抽屉,从里面又拿出一个塑料袋来——里面装的也是麸皮麦片——然后把两袋麦片倒到一起。“我这儿足够了,”他说,“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肯定够五天的了。”
他有一个保留了多年的习惯,那就是在十点左右的时候买上一品脱牛奶、一杯咖啡、一根香蕉,然后在地下广场里找一张桌子吃早餐。
不过,现在,他合上储粮的抽屉,从眼镜盒里掏出老花镜,坐下来,开始填账单。他写了几张支票,给几个信封贴上邮票,舔两下,把信封封上,然后又把笔放回胸前的口袋,接着,他起身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我不想打扰你,”我说,“你有工作要忙。”
“没有,”父亲说,“我没什么工作要做。我已经好多年不怎么工作了。偶尔会有一些事,但是,总的来说,我在这儿就是消磨时光。”
他笑笑,似乎自己都被自己这个老家伙的无厘头逗乐了。他的办公室有三扇窗户,其中两扇的百叶窗关着,不过我透过第三扇可以看见外面的天色亮了。“我所做的,”父亲站在他的文件保险柜旁边,坦白说,“就是看看报纸,或者看看书。”
他把发票收好,回到办公桌前,在我对面轻快地坐下,很是自在。“从1958年一直到差不多1998年,”他说,“我手上每时每刻都有三十到四十个案子,但是自打从那之后,数量就越来越少了,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我都快84岁了。”他摇摇头。“以前呀,”他说,“我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有大把的时间。那会儿啊,随便哪一天,我手里不但有几十个轻罪案件,还有各种各样的重罪案,杀人啊,强奸啊,绑架啊——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能把人判上很多年。我不想再像那样了,我不想再像以前那么忙了,但是我又希望能比现在稍微忙那么一点,因为我希望每天到这儿来,能有点说得过去的理由。”
父亲倚在那儿,两手的拇指塞在裤子的背带里。很多年来,他都是把头发笔直地梳向脑后,所以头顶的头发规规矩矩地形成几列,但是现在,有一小撮头发不小心蜷在了太阳穴那里,还闪着Vitalis发胶的油光。“我所希望的,”他说,“如果不算奢望的话,就是能工作得越久越好。我总说,我希望自己能在向法官做总结陈词的时候突然死掉,不过看样子是没戏了。恐怕是没希望了。不,要不了多久,老天爷就要来收我了,然后我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他的电话响了。他把电话铃声设得特别响,简直刺耳。他看看电话,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手表,说:“好吧,好吧,好吧。稍等一下。”
* * *
父亲接起电话,把座椅转过去面向窗户,好给自己一点私密的空间,而我则坐在那里,凝视着他办公桌上的一个相框——是我在他75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相框里的照片上,我和他两个人在阿拉巴马最高峰切哈山的邦克塔上。我们俩去阿拉巴马,是因为我受邀去伯明翰参加一个读书会,是关于我写的一本书,于是我便邀请他跟我一起去了,而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俩都像游客一样,租了一辆小车四处晃悠。比如说,在伯明翰民权研究所,我们俩跟在一群小朋友后面参观,看了一件又一件展品。了解罗莎·帕克斯、了解布朗诉托彼卡教育局案以及公交车抵制运动和午餐柜台静坐事件是一回事,而在了解这些历史的同时,身边围着七十名四年级的小学生,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展览路线的最后一站,是一段关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大银幕录像,播放的是他那场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呈现在我和父亲以及那群挤挤攘攘的孩子面前的——孩子们已经基本安静下来——是国家大草坪的全景画面,还有慷慨激昂的听众和那长方形的、波光粼粼的倒影池。画面里,金博士讲到“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我扭头看向父亲,只听他正喃喃自语:“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但还没有完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