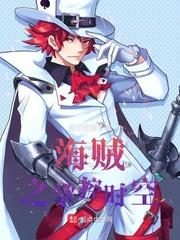奇书网>中国盗墓图志txt > 反盗墓的十大手段(第2页)
反盗墓的十大手段(第2页)
为了防止这种凶险的情况发生,作为墓主的家属,通常的做法是:一旦墓主死去,在停尸的几天内,火速派人四处打探谁家近期有人死去,埋葬何处。等一切侦察清楚,则于夜深人静之时,找亲近之人悄悄掘开死者坟墓,将尸体拖出装入麻袋,先行放置于墓主陵墓上层的棺椁中。待真正的墓主入葬之时,由一线的内情人专门给这个替身换上衣服,做一番伪装,然后盖棺走人,封闭墓门,此事就算完事大吉了。当盗墓者进入墓室并劈棺抛尸后,虽见陪葬器物较少,与自己的预测出入较大,但因一时并无明显破绽暴露,很可能借此蒙混过关,墓主得以长久地在地下安息。20世纪70年代,山东安丘石埠子农民在挖夏庄河道时,发现一大冢,墓室早已被盗一空,尸骨被抛出棺外,地上满是砸碎的陶器与瓷器,还有一些零碎的器物散落于墓室各处。众人见状,认为不过是一个通常的被盗的大墓而已,并未特别注意。想不到几天后,一个娶不到老婆的光棍青年,因整天憋得心慌意乱无处发泄,用手中的镐头在墓室内乱撞一气,突然感觉脚下不对劲儿,静下心来重重敲去,地下发出“咚咚”的声音。众人闻知,围拢上来,出于好奇,一顿乱刨硬撬,竟出现了奇迹。当一块大石板被撬开时,下面埋藏着一个完整的墓室,此室比上层略小,但建造得比上层华丽,室内高台上放有两具棺椁,棺椁旁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随葬箱,显然是一个暗室。众人见状,纷纷跳将下去,举起镐头将棺椁和随葬箱劈开,开始抢夺器物。棺内尸体保存尚好,被抢夺者拖出抛至一边,随葬器物很快被抢夺一空。极为有趣的是,那光棍青年在陪葬箱中抢得了两个坛子,打开盖一看,坛子里盛着满满的酒水,芳香四溢。有一平时嗜酒者走上前来要亲自品尝几口以示鉴定,喝了几口后大声叫好。其他的人一看墓中竟有如此好酒,纷纷拥上前来品尝。一阵混乱过后,两坛美酒尽空。几天后,安丘县文化馆文物干部闻知其事,专程前来调查,将部分被哄抢的文物收缴,但两坛酒已进入了众人的肚子,只得作罢。后来据研究,此墓为一处明代早期墓葬,两坛美酒也自然属于明代,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安丘景芝“白干酒”的前身,对研究山东最古老的酒作坊和最好的酒——景芝酒的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两坛酒点滴未剩,徒呼奈何!
这种以迷宫式埋葬来反盗墓的方式,冯素弗墓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65年,辽宁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北票县西官营子村将军山东麓冯氏陵园“长谷陵”所在地,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北燕贵族冯素弗夫妇墓。据《晋书》记载,冯素弗为北燕天王冯跋之弟,北燕国的缔造者之一,死于太平七年(415)。该墓是十六国时期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对了解当时中原和北方民族的文化关系有重要价值。
安丘董家庄墓葬下层墓室
据发掘简报,冯素弗墓分两座,同冢异穴,都是长方形石椁结构,东西向。椁顶盖以极厚的石板,椁内绘壁画,有星象、人物、建筑等内容。冯妻墓室早年被盗。椁内有一犬,棺内有几块碎骨。冯素弗墓土圹的西壁有小龛,内放陶罐、牛股、肋骨等物。木棺彩画羽人、建筑等图像,棺环、棺钉铁质而饰金,说明当时沿用汉制,皇族勋臣葬用“画棺”。令考古人员奇怪的是,当打开内棺时,“人骨无存,只见到三枚中空如牙套的臼齿齿冠,但形体很小,当是儿童乳齿”(3)。也就是说,这个棺内躺着的不是冯素弗,而是一个小孩。经现场勘查,冯素弗的骨骸自然朽毁和被盗墓贼拖出坑外抛弃毁坏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墓为迷宫式墓葬,冯的棺内尸身由一个小孩来替代,而冯本人的尸骨埋在何处,无从知晓。或许就是墓底的下屋,或许就在旁侧,但考古人员始终没有找到这座迷宫中的暗室所在位置。因而也有学者如曹永年推测,这是一座“虚墓”,用的就是潜埋虚葬的方式、方法。这类墓葬的特点是“一主二墓或多墓,有公开的虚葬墓和秘密的实际葬处”。“十六国北朝时期,在各族上层统治集团中,曾普遍实行潜埋虚葬。”而冯素弗墓则无疑是“经过科学清理的第一个‘潜埋虚葬’的实例”。(4)
所谓的“虚墓”,就是空墓,与迷宫和疑冢相似但有区别。虚墓是针对实墓而言的,一般情况下,凡有虚墓的地方,相邻处或不远处就是真正主人的墓葬。若没有这个真正的墓葬,也就不存在“虚”的问题了。晚清学者俞樾在其所撰的《茶香室三钞》中的“孔子虚墓”条下,曾提到过此事。书云:
安丘董家庄汉墓画像
宋孔传《东家杂记》云:先圣坟西有虚墓五间,皆石为之。世传先圣没,戒门弟子为虚墓。后果遭秦始皇发冢,有白兔出于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沟而没,鲁人因名其沟曰“白免沟”。按:发冢有白兔之异,必是古来神秘圣人遗迹,乃以为孔子之虚墓,则魏武之疑冢,孔子先矣。此妄说也。
俞氏之述,先是说有书记载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怕别人前来盗墓,就在真正的坟西边建造了一个虚墓。后秦始皇东巡至此,果然下令发掘孔子墓冢。因虚墓比真墓要显眼高大得多,秦始皇手下就对着虚墓挖掘起来,正挖掘间,突然从墓中跑出一只白兔,秦始皇也顾不得九五之尊的架子了,撒腿便追,一直追到曲阜以北一条沟里,兔子没了踪影为止。对这个故事,受儒学熏陶颇重的俞樾老夫子断为“妄说”。其理由是类似这种生前欺人、死后欺天的把戏,不是圣人孔子能做出来的,只有乱世奸雄如曹操者才能想得出、做得来,故斥为妄说。
不过,历史上确有以虚墓伪装,掩人耳目的事实。著名史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梁纪十六》高祖武皇帝“太清元年”一条下记载:“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从记载来看,尽管用了虚葬的方式,且仿效秦二世胡亥残杀修建秦始皇陵地宫工匠的方法,以防机密外泄,但该墓还是没有逃脱被盗掘的命运。悲夫!
既然设置虚墓仍不能阻止盗贼前进的脚步,有聪明狡诈者干脆就来个疑冢式,以观后效。所谓疑冢,就是比迷宫和虚墓发展前进了一步,或者说方式、方法更加极端。其特点是秘密建墓和秘密埋葬,让世人弄不清、辨不明真正埋在了哪里。当年楚平王葬入湖中即疑冢的先例之一。在中国民间名气最大、流传最广的疑冢的设计者,当数三国时的曹操,他所设置的“七十二疑冢”,堪称古往今来疑冢之最,因而也被历代文人墨客所重视,并以此编出了许多离奇的故事。
且说在秦末农民起义引发军阀混战而借机割据岭南之地的南越王赵佗,在人生的晚年,出于对国家前途未卜的忧虑,以及对盗墓者的恐惧,让自己的心腹重臣、丞相吕嘉,挑选一批得力人马,在南越国都城番禺郊外的禺山、鸡笼岗、天井等连冈接岭的广袤地带,秘密开凿疑冢数十处,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藏身之所,以让后人难辨真伪而不遭盗掘。赵佗魂归西天后,其孙赵眜与吕嘉以及几位心腹臣僚做了周密严谨的布置后,于国葬之日,派出重兵将整个城郊的连冈接岭处包围得密不透风。稍后,无论是规制还是规模都极为相似的多个灵柩,同时从都城番禺的四门运出,行进的送葬队伍在灵幡的导引下,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左右盘旋,神秘莫测。当运出的灵柩全部被安葬完毕后,除赵眜和身边的几个重要大臣外,世人无一知晓盛放赵佗遗体的灵柩以及陪葬的无数瑰宝珍玩到底秘藏于何处。
黄武四年(225)春,称帝不久的吴主孙权,在得知赵佗死后曾葬有大量奇珍异宝并一直未被后人盗掘时,立即命将军吕瑜亲率5000名精兵,翻越雾瘴弥漫的五岭,抵达南越国故地,大张旗鼓地搜寻、盗掘南越王家族,特别是南越王赵佗的墓冢。由于南越王赵佗及其后世子孙的墓冢极其隐秘,吕瑜和手下兵将于番禺城外的连冈接岭处伐木毁林,凿山破石,四方钻探,在折腾了半年后,总算找到了赵佗曾孙、南越国的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葬,并从这座墓穴深处盗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等大批珍宝。令孙权感到遗憾的是,直到吕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岭南返回东吴腹地时,始终未能获取有关赵佗和其孙赵眜的墓葬秘所,甚至点滴的线索也没有。
南越王墓石门
孙权兵发岭南掘冢觅宝的行动,再度引发了当地掘冢刨墓的风潮,当吕瑜的大军撤出后,整个岭南大地盗贼蜂起,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连绵的山岗野岭,并绞尽脑汁四处访凿,希图搜寻到连孙权大军都无从探访到的赵佗以及赵佗家族的墓葬,但让盗贼们恼恨和失望的是,无论他们怎样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辉煌的梦想一个个变成泡沫化为乌有。
1983年6月9日,一伙民工在广州郊外号称象岗的山上刨土炸石,无意中炸出了赵佗之孙赵眜的墓葬。这座墓葬保存完好,墓道填塞巨石,以石制顶门石封闭厚重的石门。可能当年赵眜与他那老谋深算的爷爷一样,在死前设了疑冢,墓葬一直不为外人所知,从而躲过了继孙权之后千余年来盗贼的搜寻与探试。而关于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在何处的问题,广东方面的考古学家借用先进的探测技术,已在广州城内城外可能想到的地方连续不断地寻找、钻探了50多年,仍未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可见这位南越王设疑冢是历史上最为成功者之一。
八、储水藏棺设置暗器。在通常情况下,陵墓地宫要选择干燥之地,严防地下水渗入,若有水渗入则被视为“不吉”。明代万历皇帝位于昌平十三陵区的定陵,在修建时因地宫渗水,万历帝几次前往视察,心怀恼怒,差点改换位置。而清代的道光皇帝在清东陵修建的地宫,渗水严重,惹得这位皇帝龙颜大怒,最后下令拆毁已建好的陵寝,索性跑到北京之西的清西陵重新建造了陵墓。因帝王的陵墓地宫大多要深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渗水成为必然。为解决这一难题,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在地宫内设排水系统,并以管道将水引出,排入陵墓周围的低矮处或河道中。这种方法,至少从秦始皇陵地宫的修建就开始应用,后来历代帝王陵寝多效法此道。如此这般,又引出了新的麻烦,墓主本意是用管道疏通渗水,结果被人发现,沿着水管直接掘进了墓室,所料未及,适得其反,悲惨的后果可想而知。
出现这种情况的,自然是中小型墓葬,若是帝王陵墓,其排水设施较为复杂,沿着管道盗掘要比从其他位置入手困难得多。当年秦始皇陵“穿三泉”,地宫渗水颇多,处理的方法就是用陶制管道,由地宫通往离陵墓几里远一个叫“鱼池”的大渊中释放,直到现在,“鱼池”仍可见水。据说当年秦二世关闭墓门后,数百工匠被困在地宫活活憋死,只有一个青年石匠,设法钻入管道内向外挣脱,居然爬到了“鱼池”中,成为数百工匠中唯一的幸存者。
秦始皇陵地下排水管道
为了杜绝盗墓者沿着管道进得墓室,又无其他办法将水排出,有人索性不再顾及,任其自然。这样一来的后果是,用不了多久,墓坑内就会积满渗水,深度可达几米。若是空间宽敞高大,水的浮力足以将棺椁漂起。从已知的情况看,湖北擂鼓墩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墓室水深达3米余,考古人员发掘时,陪葬棺全部浮起,或侧翻,或倒扣,无一完整者。而清东陵中的康熙、乾隆、咸丰、慈禧等陵墓被兵匪打开时,地宫内水深皆在2米以上。三位皇帝的棺椁俱浮起且已游走别处。或许正是鉴于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原因,有的墓主索性来个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将棺椁浸入水中,并设置暗器,以防盗墓者入侵。于是,一种隐蔽的轮式飞刀应运而生了。
通常的方法是,在依山之地或高坡下挖墓坑,有的为崖式竖穴,有的为券洞样式,形式不限,大小不限,有的券洞墓只有一层石门,有的多达三四重石门,这与墓主的财力、地位有关,与所运用的方式、方法无关。但这类墓葬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当地下涌出水流或渗出清水时,不像秦始皇陵地宫和其他帝王陵地宫一样填置塞石和以白膏泥等黏性物堵塞(最明显的是明十三陵万历皇帝的定陵地宫因渗水而填塞大量塞石),而是任其自流,直到水位达到平衡为止。外观看上去,与水库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中间用石或木墙隔开,四面置厚重石墙,上有平式或券式封顶而已。就是这样一个蓄满水的墓坑,若设置暗器,比其他反盗墓方式要厉害得多。
既然是水库式墓穴,墓主人的棺椁一般为石制,至少最外层的椁是用厚重的石板制成,然后用上等木料制作一层或多重棺置于其内,木棺石椁的缝隙用黏性胶状物漆封其间,以阻止渗水入棺毁坏尸体与陪葬器物。若封闭得好,这类棺椁对尸体的防腐性能和防盗作用远优于纯粹的木棺木椁。据《史记》记载,有一次,汉文帝携邯郸籍宠姬慎夫人到霸陵视察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工程,群臣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当文帝坐在霸陵上面的一侧向北眺望时,心生感慨,遂命慎夫人鼓瑟,文帝倚瑟而歌。未久,文帝惨凄悲怀,对群臣感慨地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尽管在臣僚张释之一番劝说下,最后没有用石椁安葬,但当时汉文帝还是相信石椁在防盗这一点上明显优于木椁。由于霸陵“因其山,不起坟”,地面上没有封土,陵墓排水成了个重要问题。《长安志》卷11引《关中记》中记载:霸陵之上“为池,池有出道以泻水”,这该是霸陵的部分排水设施。后因排水系统遭到堵塞,陵内地宫成为一片汪洋泽国。许多年后,决堤的渭河水冲进霸陵地宫,文帝的尸骨与随葬器物随着河水或入污泥或入了东海。假如当年文帝以石椁裹尸,若盗墓贼手下留情,或许不至于落个尸骨随水漂流的悲惨下场吧——当然,这个设想仍取决于盗墓贼进入地宫时的心境和对待墓主的态度。
汉文帝没有用石椁埋葬,但用石椁者历史上不罕见,并有无数石棺石椁出土。其实这类葬具并没有什么稀奇,若有奇者,当奇在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一面。唐人牛僧孺撰著的《玄怪录》中,在卷三有一个“卢公涣”的故事,说的是黄门侍郎卢公涣,为明州刺史。他所治下的邑翁山县,山谷沟壑众多,常有盗墓者出没其中。有一盗墓老手在山下道路的车辙中偶然发现了一块花砖,揭起一看样色,立即意识到不远处定有大墓藏于山野草泽之中。经过勘察,在离道路约三四十尺的地方,确有一墓冢掩入草莽泥沼,由于年代久远,已不被世人所知。盗墓老手对此墓极感兴趣,认为墓中必有奇珍异宝。乃结10余人,于县衙投状,请求在山下道路边住居开荒种地。县令不知是计,接到贿赂的金钱后,很痛快地批准了这一请求。盗墓贼开始在墓葬的周围种麻,以掩路人耳目。待麻长到齐腰高时,贼娃子便结伙挖掘起来,只两个夜晚就挖开了隧道,渐渐进入圹中。接下来,便出现了惊险悬疑的一幕:
翌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一扇开,有黄衣人出,传语曰:“汉征南将军刘,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及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恋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瘗货宝,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便不已,当不免两损。”言讫却复入,门复合如初。
盗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不听。两扇欻辟,大水漂**,盗皆溺死。一盗解泅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黄门令覆视其墓,其中门内,有一石床,骸枕之类,水漂已半垂于下。因却为封两门,窒其隧路矣。
这个故事若除去玄乎其玄的迷信与神话色彩,其实就是一个蓄水墓,用水以防盗。防盗的方法属于比较简单的一类,即在崖洞的末头以石筑坝蓄水,坝有门洞可关闭,两旁设机关,以控制门洞之门。又以绳索系于机关与外界相连,一端拴于墓门之后。当盗墓者启动墓门之时,绳索拉动坝上机关,坝门开启,大水汹涌而出,将盗墓者溺毙。为什么从墓中开门而出的“黄衣人”要对盗墓贼说如果不听劝阻,则“不免两损”呢?这说明此墓并不完全是一个“水洞子”,只是后半部蓄水,而前半部则是干燥的,所安置的石床之类陈设专为主人盛放尸体之用。若将蓄水放出,无疑将呈水漫金山之势,这是墓主人,确切地说,是墓主在世修建此墓时不愿看到的结果。但事已至此,再无退路,门开则水出,盗墓贼被溺毙,墓主人的寝室也就成为一个小型水库了。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汉征南将军活着的时候,与敌人周旋的战略战术并不咋的,可能只会在上游掘堤,来个水淹三军之类的常招,并没有其他异乎寻常的计谋,应该属于庸才将军一类。因而,机关算尽,最终自身不保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历史上,真正有计划蓄水并藏暗器的陵墓,比这位汉征南将军设计巧妙得多。如上所说,蓄水墓的棺椁为石料所制,密封放于石床之上渐渐被地下水浸没。当陵墓建成后,便在甬道和墓室的地面铺设铁木合成的地板,地板之上斜插尖状刀片,刀片有规则地成排成行遍布墓内的各个角落。在刀片之间,每隔几尺安装一部由叶片刀组成的转轮。转轮如同北方常用的链式水车,或如南方的龙骨水车。每三部转轮为一组,相互贯通相连,下设翘板,板与轮上的链条相接。翘板之上又有翘棍,每棍约三尺长,暗藏刀锋,不规则立于翘板之间,上有链与轮相连。也就是说,整个墓内遍布水车样的带刀转轮与丛林状的翘棍刀,一旦盗墓者涉水而入,必踏动翘板,或擦动棍刀,板、棍一动,转轮即动,飞刀在水中旋转开来,像切割红烧肉一样将入侵者的身子骨一刀刀划开,在鲜血涌动与惊恐的哀号声中,进入者非死即伤,再也难有作为。为了诱敌深入,墓中还根据盗墓者贪婪的本性,专门设置明器以吸引对方眼球。即故意把一件或数件器物放于明处,以绳索拴之,或吊于顶,或放于壁上。绳的另一端则与带刀的转轮与暗藏锋刃的翘棍相连,盗墓者一看有宝物在前,便忘乎所以,上前抢夺,结果是绳断板翘,转轮滚动,飞刀旋转,翘棍摇晃,盗贼难有逃生之机,必死无疑。
九、填沙防盗。即在墓道和墓室周边填塞细沙,这个方法很简单,却是中国人独到的发明创造。盗墓者之所以在一夜或几夜之内就顺利进入墓室,一个重要原因是打洞,唐代之前打圆式洞,唐之后打四方洞,这一规律已经成为鉴定盗墓年代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何以有如此之分法?答曰,唐之前多为竖穴墓,也就是长沙马王堆那种类型,在山包或平地直接向下挖个大坑,然后在坑中放上棺椁,用木板封顶,上面覆土。因这类墓葬土质较厚,根据物理学原理,挖的时候必须是圆形洞才不易塌陷,方洞易塌。唐之后一般多为券洞墓,除像武则天那样以山为陵外,多是砖石结构,覆土没有唐之前那样深厚,中途塌陷的概率较小,因而可挖方洞,毕竟方洞活动起来更方便些。但无论是圆洞还是方洞,都是建立在泥石堆积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打洞挖坑。若周围不是土石而是一片沙漠,此事就难了。
发明者恰恰抓住这个特点,在墓道或墓周边填沙,少者几吨,多者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盗墓者若想进入墓室,就必须与填沙打交道,或者说只能一点点地向外掏沙。沙呈软性,掏出一点,周围之沙立即涌将出来补充,如此循环往复,沙涌不绝,除非将所填之沙全部掏尽,否则不能进入墓道与墓室。宋人程大昌所撰的《考古编》卷九有一条就涉及这类情形。书云:
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此不可晓然。尝记唐人有一书,备载乾陵之役,每凿地得土一车,即载致十里外,换受沙砾以回,实之方中,故方中不复本土,而皆积沙壅之。此防盗者之巧思也。土受润则相著,穴之数尺,隧道可径入矣。沙砾散燥,不相粘著,非尽徙而他之,虽欲取径阙隧,无由而可。凡盗之至于发陵者,类皆乘乱承间,暂至亟去,无能持久徐运,以虚其积者也。
乾陵是否填沙尚有待考证,但这填沙的方法以及盗墓贼遭遇的尴尬,皆清晰明了地道了出来。盗墓者往往是趁天下纷乱之机进行刨坟掘墓的勾当,自然不会长久持续在一个地方行动,且如此多的沙土,要运到外部也实在不便掩饰。
正是鉴于类似盗出的土难以处理,且易引起好事者的注意并有被官方捉拿下大狱的危险,程大昌的《考古编》在论述盗墓贼遇到填沙时,总结性地说:
故虽有剧盗,穿穴不竟,必皆舍去。人见其不竟也,遂从而神之,以为有风雨驱迫,其实不然也。然设此巧者谁乎?锢铜漆絮,费而不工矣。
当盗墓贼见流沙不止,无有穷尽时,因情势所迫,只得停止挖掘另觅他处,看来这填沙防盗的手段的确含有中国人特有的巧妙智慧。据说,民国时候,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下令盖了一座庞大的监狱,专门关押与他在政治上作对的人,狱内分成若干不大的房间,墙壁和屋顶采取古为今用的方法,用细沙填塞。若有穿墙越狱者,只要拆掉一块石头,细沙纷纷涌出,很快就会被看守者发现。因而这座监狱凡20年风云变幻,无一越狱成功者。
十、机弩飞箭、伏火毒烟,多兵种联合防盗术。传统的反盗墓手段,除石椁铁壁以求坚固,储水、塞石、积沙以防盗凿,以及各种杀伤性方法外,随着盗墓与反盗墓者的博弈,结构和技术最为复杂、杀伤力最大、集一切传统防盗术之大成的多兵种联合防御体系相应诞生了。这一防盗体系,从古代记载的几个案例中可见一二。
唐人段成式有一部《酉阳杂俎》,专门搜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奇闻趣事以记载,在“尸穸”条下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
这是典型的毒气防盗术,与秦始皇地宫的水银相同,但比水银的爆发力强得多,杀伤力也大得多,弱点就是逞凶一时,不能持久。相反,以水银为毒气要长久得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尽管水银的毒性持续时间长,但若散发开来,蓄存于墓内飘浮于空间中的水银浓度越来越稀,数日之后,对人的毒害就微乎其微了。出于安全考虑,盗墓者让一只狗先行进入墓内试探,不失为一个保全的方法。到了1956年,现代考古人员发掘十三陵中的定陵时,打开地下玄宫大门,恐内部有弓箭伏毒,不敢入内,只好找来一条狗和一只鸡放入墓中,经试探无险情和毒气放出后,方进入墓道开启第一道石门,最后进入玄宫后殿,找到了万历帝后的梓宫。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还曾引《水经》言:“越王勾践都琅琊,欲移允常冢,冢中风生,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地,内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其机也。”这个故事已有点多兵种联合的味道了。而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段氏在同一部书中所讲的另一个故事,可谓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集团军式的典型案例。书中卷13“尸穸”条下说:有一个叫李邈的判官,老家在汉高祖陵附近,后李氏罢官归家住居,遇一盗贼,贼自称近来在李判官的老家10里地左右开一古冢,“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烊粪沃之,方开”。
按照盗贼的说法,墓中石门缝隙用铁汁浇铸,以防盗墓者打开。这个防盗招数并无奇特之处,奇则奇在盗墓贼竟以熔化的粪浇之。数日之后,门竟被打开了。何以用粪来浇灌就能打开铁水铸就的石门?道理很简单,现代化学分析证明,粪的酸性强度很高,对铁质具有很大的腐蚀溶化作用。可谓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铁汁遇到了粪,形同豆腐遇到了卤水,只有被凝固或被溶解的份儿。因而数日之后铁汁被腐蚀溶化,石门洞开,只待盗墓者进而取宝了。意想不到的是,一件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情随即发生了。书中接着说道:“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机关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集。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为沙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