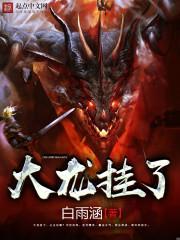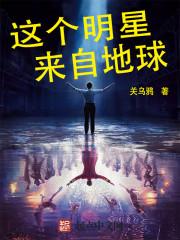奇书网>叶圣陶传记500字 > 答周道通书(第2页)
答周道通书(第2页)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①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注释】
①《中庸》篇语。
【译文】
来信写道:“存养要在事上磨炼,一天之内,不管有事没事,只要一心培养本体。如果遇到事情有了感触,或者自己有了感触,心里既然有了感觉,怎么能说无事呢?但是根据情况仔细考虑一会儿,大体觉得事理应当如此,只是当作没什么事一样对待,尽我的本心罢了。然而仍然会有事情处理得尽善和未尽善,为什么呢?又有时事情来得多,需要按顺序处理,常常因才力不足,就被事情所困扰,即使极力坚持也感觉精神疲惫衰弱。遇到这些情况未免要退下来反省自己,宁肯不做完事,也不能不存养本心。这样对吗?”
所说的功夫,对于道通你来说,也就是这样了,然而未免还有些出入。凡人求学,终身只做这一件事。从小到老,从早到晚,不论有事无事,只做这一件,就是所谓的“必有事焉”。如果说“宁肯不做完事,也不能不存养本心”,却仍然是两件事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来临,只要尽到我心中的良知来回应它,就是所谓的“忠怒违道不远”的意思。凡是害怕将事物处理得有尽善有未尽善之处,以及有困扰失序的问题的,都是因为在意毁誉得失,而不能确实地实现良知。如果能够确实地实现良知,然后看到平日里所谓善的未必是善,所谓不善的,恐怕正是因为在意毁誉得失,自己毁掉了良知。
【原文】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来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译文】
来信写道:“关于致知的学问,春天里再次得到先生的教诲不胜受益,已经很清楚应该怎样用功,觉得比从前更加简易。但是我心中认为对初学者讲说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格物’的意思,让他们明白下功夫的地方。本来对于‘致知’和‘格物’应该是一起用功的,但对于初学者来说,不知道怎样下手用功,还是先讲‘格物’,才明白‘致知’。”等等。
格物是致知的功夫,知道致知就是已经知道格物。如果不知道格物,就是连致知的功夫也不曾知道。近来有一封书信,与朋友谈论这件事,非常详细,现在给你寄去,仔细看看,自然能够明白。
【原文】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辨者尚未已。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气象何等从容!尝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师又可恶乎?
【译文】
来信写道:“如今为朱、陆争辩的还大有人在,常常对朋友们说圣学不昌明已经很久了,并不需要枉费心力来为朱、陆的学说争论是非,只凭着先生‘立志’两个字来指点人。如果这个人真能辨明这个志向,决心要学习圣学,那么他已经大体上明白了,朱、陆的是非虽然不能辨明,他自己也能感觉出来。又经常看到朋友当中,有人看到旁人非议先生的言论,就非常生气。过去,朱、陆两位先生遗留给后世众多争议,这说明两位先生的功夫有不够纯熟的地方,明显有意气用事的弊病。像程颢先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看他与吴涉礼谈论王介甫的学问时,说:‘请把我的观点全部告知介甫,即使对他没有益处。也一定对我有益。’何等从容的气度!曾经看到先生给别人的书信中,也引用这句话,希望朋友都做到这样,是这样吗?”
这段话讲得非常非常对,希望道通你能够告诉所有的同道们,每个人只议论自己的是非,不要去议论朱、陆的是非。用语言来诽谤他人,这种诽谤很肤浅。如果自己不能亲身实践,而只是随便听听说说,唠唠叨叨度日,这是用行动诽谤,这种诽谤就更严重了。凡是现在天下讨论非议我的,如果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也都是在与我磨砺切磋,对我来说也无非是警惕反省、增进品德的地方。从前的人说攻击我的缺点的人是我的老师,老师难道是能厌恶的人吗?
【原文】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①,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注释】
①告子语。见《孟子·告子》篇。
【译文】
来信写道:“有人引用程颐先生‘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问朱熹先生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不是性?朱熹先生回答道:‘不能说,是因为没有性可言;不是性,是指说了之后,就不可能没有气掺杂在里面了。’两位先生的话,我没能明白,每次读到这里,都有这个疑惑,向先生请教。”
“生之谓性”,“生”字就是“气”字,也就是说“气即是性”。气就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这样人性已经偏到了一边,不是本原了。孟子的性善论,是从性的本原上说。然而性善的端倪,一定要在气上才能开始呈现,如果没有气也就无法看到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是气。程颐先生说的“论性不论气,不全面;论气不论性,不明白”。这也是因为做学问的人只看到一方面,只能这样解释。如果能看明白自己的天性,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没有性和气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