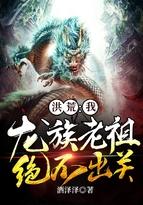奇书网>叶圣陶 精读指导举隅 > 02(第1页)
02(第1页)
02
【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住重点,说“致良知’当下就可以实际用功,所以我专门讲解“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其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没有一点点私心妄意,就是“正心”。踏实地致良知,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一点点私心妄意,就自然没有助的毛病。因此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是为告子的毛病下的功夫。告子强制内心,是“助”的毛病,因此孟子专讲“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的毛病,也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外,不知道从自己内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会这样。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中“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能够洞彻明白,是非自然都能纤毫毕现,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来学者大有功劳,然而这也是对症下药,从大体上说,就不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极为精一简易,上下贯通,万世都没有弊病了。
【原文】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圣贤讲学,大多是随时随事而定,虽然他们的说法好像各不相同,但关键功夫,都是一致的。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这个本性,只有这个天理,只有这个良知,只有这一件事而已。因此凡是在古人论学上虚讲功夫的,就不必再掺杂搭配,自然没有不融会贯通的,如果需要掺杂搭配,那就是自己的功夫还没有明澈。
近来有人说“集义”的功夫,一定要搭配上“致良知”然后才能算是完备,这就是“集义”的功夫还不明澈。“集义”的功夫还不明澈,就刚好成为了“致良知”的拖累。认为“致良知”的功夫,一定要搭配上“勿忘勿助”然后才能明白的,就是“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了彻。“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了彻,就刚好成为“勿忘勿助”的拖累。类似这些,都是字义上牵强附会的解释,求得融会贯通,而没有在自己的实际功夫上体验,因此论证得越精确,偏离得就越远。
文蔚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疑问,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学说,还不时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说的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出现迂回曲折的行路的情况,等至功夫纯熟之后,这种情况便自然会消失。
【原文】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诙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译文】
文蔚你所说的“致知”的观点,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上去寻求,就感到有所遵循。这里最能看出你近来真切笃实地下了功夫。但你自己从这里下功夫倒也无妨,自然有得力的地方。如果把这当成定论去教导人,却难免出现用药不当反而致病的情况,这不能不同你说明白。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良知的自然明觉的呈现就是真诚恻隐,这是它的本体。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去侍奉父母就是孝,尊敬兄长就是悌,辅佐君主就是忠,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也就是侍奉双亲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如果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所以,能实现辅佐君主的良知,就能实现尊敬兄长的良知。能实现尊敬兄长的良知,就能实现侍奉双亲的良知。这不是说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实现,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如果这样,就又脱离了本原,在细枝末节上探求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它的发挥和呈现,自然完备充足,无来无去,不需要向外假借。但是它发挥和呈现的地方,却有轻重厚薄的区别,丝毫不能增减,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然轻重厚薄丝毫不能增减,但良知原本只是一个。虽然良知只是一个,但其中的轻重厚薄又丝毫不能增减。如果能够增减,如果必须向外探求,那就不是真诚恻隐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无形无体,无穷无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的原因。
【原文】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①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②者也。
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工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注释】
①《孟子·告子》篇,曹交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答语中有此语。
②施诸后世而无朝夕,《礼记·祭义》篇语,言无一朝一夕或外此也。
【译文】
孟子说的“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这是在人的良知最真切淳厚、不容蒙蔽的地方提醒人。在忠君、交友、爱民、爱物以至于动静言默的时候,都只是实现他那种一念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也就自然无处不是道了。天下的事虽然千变万化到无法穷举的地步,但只要用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去应对,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漏缺失的了,这正是只有一个良知的缘故。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良知之外,没有别的良知可以实现。因此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就是“惟精惟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后世推行也不会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