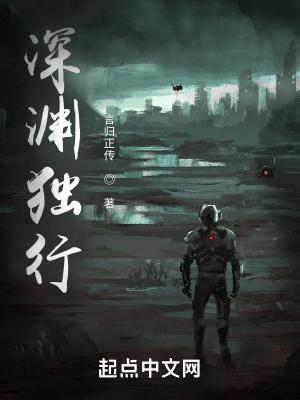奇书网>景德元年大宋王朝1004年的历史大变局 > 南迁还是北征(第3页)
南迁还是北征(第3页)
寇准又搬出了宋真宗的先人。(12)
这时候,寇准、宋真宗、陈尧叟、王钦若四个人的心里各有各的想法。看着眼前的寇准、毕士安、王旦、王钦若、陈尧叟等人,宋真宗不知何去何从。
宋真宗也明白寇准的意思,但寇准的这番话已经是老生常谈,听的次数多了,宋真宗也就腻烦了。对于腻烦了的事情,宋真宗自然不愿意再去理会。
宋真宗明知道南迁可能引发国家动**,可寇准的警示完全无法引起宋真宗的警觉。此时的宋真宗,心里是紧张的,比起隔江而治,在边境督战更加凶险,说不定还会命丧黄泉。
这种情况下,宋真宗觉得划江而治也不一定不好。当然,眼下宋辽两军虽然摩擦不断,但还没有到紧急万分的时刻。
不久,前线又传来消息。这个消息,让举棋不定的宋真宗再次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消息称,辽军已经过了瀛州,直逼贝、魏二州。(13)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让宋真宗惊慌失措。毕竟贝、魏二州,已然到了黄河边上。
宋真宗赶紧召集群臣商议,再不商议,辽军过了黄河,汴京就被围了。还是之前的两种意见:南迁和亲征。这两种意见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论证,宋真宗还是没有办法决定采用哪一种。
这时候的宋真宗更倾向于南迁。这是非常保险的做法,即使辽军攻破大名,甚至攻破澶州,只要自己到了江南或者成都,辽军依然对他无可奈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是,宋真宗这就决定南迁了吗?很显然不是,因为朝堂之上还有主战的一派。
此时的寇准,为了促成宋真宗亲征,已经想尽了办法。他迫不及待地继续说,官家这次若能亲征,大名府自是亲征的最佳地方。毕竟大名府距离前线最近,鼓舞士气,就应该到大名府去。
寇准还分析了大名府当前面对的不利局势:辽军此番南下,大名府是首当其冲的重要市镇,一旦被辽军攻破,那么整个黄河以北就只剩下澶州了。无论如何,亲临大名府,已是当务之急。
陈尧叟和王钦若等人鉴于寇准这样霸权专横,也不好再动员宋真宗南迁,只能闭嘴。
这时候,宋真宗把目光转到了毕士安身上,想听听他的意见。相较于寇准而言,毕士安是自己人,当时宋真宗任命毕士安和寇准同时为相的时候,就是考虑到他们两人一个老成持重,一个大胆勇敢。所以,让他们为宰相,互为补充,最合适不过。
毕士安虽然赞成宋真宗亲征,可并未像寇准那样激进。毕士安建议宋真宗亲征到澶州便可以了。(14)大名府充满了未知因素,不宜前往。此时,寇准眼巴巴地看着王继英,希望王继英可以站到自己这一边,但王继英却站到了毕士安一边。
听到朝中双宰相都建议亲征,其他大臣也只能随声附和。寇准此番据理力争,已然产生了效果。
看到宋真宗并没有表态,眼神阴郁,寇准选择了折中的态度,便退让一步说,亲征这件事,肯定要执行,如果官家您不想去大名府,那您就到达澶州吧。
既然两位宰相都支持亲征,宋真宗还真没法再准备南迁了。大臣尚且不惧死,皇帝难道要如此胆小如鼠吗?
然而,亲征对宋真宗而言,还是有畏难情绪的事情。
这些年来与辽军对打的过程中,宋军损失惨重。二十多年来,宋朝很少能打胜仗。所以,每次防御之策制定时,朝廷都只让边境守将驻守在宋境内,辽军若不主动来攻打,宋朝守将是不能去招惹辽人的。
再说,每次战火一起,粮草辎重就得跟上。尤其是咸平年间,宋辽几乎年年都有战争,而宋朝应付一场规模不算太大的战争,都要消耗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与辽国这些年的战争,宋朝的国库已经有了空虚之感。且辽宋之间,宋军就一定比辽军更胜一筹吗?
这在宋真宗看来未必。这一点儿也不难理解,宋真宗是个务实的人,自小在宫廷深苑里长大,没有见过战争,更没有主持过战争,他不像伯父赵匡胤可以自己打下江山,更没有父亲赵光义的勇气,能够亲征契丹。
就宋辽之间的战争而言,宋真宗自己不敢妄下定论,他也害怕战争的残酷。赵光义的箭伤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思想负担,如果不是赵光义亲征辽国,也不至于中箭,指不定此时还是皇帝。然而,这些一切,都没办法假设。
宋真宗越来越不敢想象。此时宋真宗内心是纠结的,他想和,可没有更多的干部基础,很大一部分人都坚持他御驾亲征。只有这两个南方的臣子,给他提出了南迁的建议,却势单力薄,无法与其他大臣的意见抗衡。
最终,宋真宗决定亲征澶州。此时,辽军攻打大名府的消息,传到了宋朝内部。当下,宋真宗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还是寇准充当了主角。寇准觉得,这次辽军攻打大名府,必然动用了所有兵力。尽管大名府的天雄军锐不可当,可还得做最坏的打算。寇准建议:必须给大名府派出一位宰相级别的人压阵,方能保住大名府。
宋真宗以为寇准要亲临前线,指挥大名府的战斗,那样自己怎么亲征?但寇准所说宰相级别之人,也包括参知政事之内的副宰相。
那么,参知政事都有谁呢?王钦若和王旦。
宋真宗似乎明白了寇准的言外之意,就是要在王旦和王钦若二人当中,选一人去镇守大名。
此时的寇准心里已然有了人选。他看中的人,是王钦若。于是,寇准对宋真宗说,王钦若做事素来干净利落,颇有能臣风范,不如将王钦若派到大名府去压阵。
宋真宗看了看王钦若,似乎在问王钦若:你的意思呢?王钦若因为建议宋真宗移驾江南,被寇准定性为该杀之人。此刻,他依然没有任何为自己争辩的理由。王钦若似乎也很明白,寇准提议将他调到大名府,让他去压阵,自然是想将他从宋真宗身边支走。(15)
看透了寇准的目的,王钦若便主动申请去大名府压阵。宋真宗很欣慰,既然王钦若愿意去,那就让他去。王钦若拜谢了宋真宗,便准备去大名府任职。但是,王钦若内心对寇准的仇恨越发潜滋暗长。这种仇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王钦若心中生根发芽。
其实,寇准之所以这么急不可耐地将王钦若支走,依然是担心在亲征路上王钦若再次怂恿宋真宗南迁,到时将会带来诸多麻烦,这不是寇准愿意看到的。因此,这次寇准是故意设计将王钦若调离朝廷。
如此,一切亲征事宜算是处置妥当了。然而,此时首相毕士安却病了,且病得不轻。尽管如此,毕士安依然希望跟着宋真宗去亲征。但宋真宗鉴于毕士安身体不便,便将他留在汴京,一方面可以让毕士安好生休养,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及时处理汴京相关事宜。
此时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当时,有懂天象的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天象: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对于这个天象,洞悉其中奥妙的人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宋朝这次出兵会不利,其二是会有大臣得重病。(16)然而,宋朝已筹备多时的亲征,此时不能因为一个天象就此作罢。
最终,毕士安将天象之事揽在了自己身上。毕士安表示,如果真要有大臣病重,那就是他吧。反正他已经病重了很久,也不在乎。只要能为朝廷承担天象预兆的后果,自己万死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