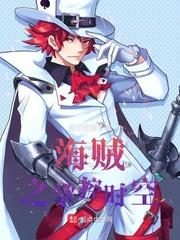奇书网>三毛流浪记大千世界 > 别哭骆驼(第2页)
别哭骆驼(第2页)
在手忙脚乱的招待中,三毛渐渐迷茫起来: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问我沙漠逃难的情形,没有一句话问我们那个被迫丢掉了的家。婆婆没有问一声儿子未来的职业,更没有叫我们回马德里去,婆婆知道马德里付了一半钱的房子,而今荷西没有了收入,分期付款要怎么付,她不闻不问。她、姐姐、姐夫,来了一天了,所谈的不过是他们的生活和需求,以及来度假的计划。我们的愁烦,在他们眼里,可能因为太明显了,使得他们亲如母子,也不过问,这是极聪明而有教养的举动。比较之下,中国的父母是多么的愚昧啊!中国父母只会愁孩子冻饿,恨不能把自己卖了给孩子好处。
我自己妈妈在中国的日子跟我现在一色一样,她做一个四代同堂的主妇,整天满面笑容。为什么我才做了五天,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对荷西的家人尚且如此,对外人又会怎么样?我自责得很,我不快乐极了。(3)
然而,这场持续数日却漫长如一个世纪的战役结束后,三毛又坦然了。她不再去思考如何与亲戚相处、处理接踵而至的家务,因为这里又是她的家了——没有其他需要烦恼的事情,她只需让自己愉悦。
经济越发拮据,如果不工作,怎样维持生活呢?荷西只得回到撒哈拉去,在硝烟中搏命换取家用。三毛的恐惧与忧郁一日多过一日,终于在某一天出了车祸,不得不卧床。荷西毅然丢下刚刚涨薪的工作,回到她身边。
他太了解她,知道自己必须守护在她身边,她方才安心,正如结婚前某一个普通的日子,她只是呕吐而已,他却在床边看护良久,直到她痊愈。
其实早在婚前,荷西就曾小心翼翼地询问过三毛的心意:“你想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三毛自称唯恐荷西不愿娶她,忙不迭地表白心迹:“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如果是你)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吃得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4)
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三毛没有稳定的收入,荷西的工作又充满危险,如同世上任何一对普通的夫妻,婚姻里的两个人都会因为各种琐事发生争吵。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双方的意志、想法要完全重合,几乎不可能,然而不管怎么争吵,感情是不会变的。因为三毛对荷西非常依赖,不愿他离开,所以三毛与荷西发生了争执。
失业的荷西依旧坚持着大男子主义的原则,不愿靠妻子微薄的薪水供养。荷西向世界各地寄出求职信,尽管他的职业素养很高,工作能力很强,但仍旧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
“两个人常常失眠,黑暗中拉着手躺着,彼此不说话。”三毛焦虑至极,甚至写信给蒋经国,希望为荷西这位中国女婿谋得一份差事,却得到了表达歉意的回复。
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仍旧没有消弭。在远离城镇的海滨社区“小瑞典”,他们居住在退休老人中间,觉得“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他们在渔船到来时帮忙拉渔网,与朋友爬山露营,营造自己的小花园、小菜园,夏日里每天都要在海滩上散步,到海里潜水。不出门的时候就看看书,听听音乐,写写文稿,捡捡石头。每天只吃一餐,腹中饥肠辘辘,但见到推销西班牙文百科全书的年轻人,仍会不惜高价买下一套来,算是帮他的忙。(5)
善良的傻子顾不上自己空空****的肠胃,还要拿出有限的钱财普度众生,真是可敬又可怜。
三毛原本想要离群索居,不再重复沙漠里被邻居烦扰的生活,却因为这份改不了的天生好心,又一次落了空。不过,三毛其实是享受的,她太需要爱和关注,即便远离人群,她仍旧拥有人们的爱护,与沙漠里一样,“在此我的朋友很多,大家都对我好,所以我很受疼爱,精神上不觉孤独”(6)。
(1) 引自《亲爱的婆婆大人》,收录于三毛作品集《稻草人手记》,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2) 引自《亲爱的婆婆大人》,收录于三毛作品集《稻草人手记》,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3) 引自《这种家庭生活》,收录于三毛作品集《稻草人手记》,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4) 引自《大胡子与我》,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哭泣的骆驼》,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5) 引自《百科全书》,收录于三毛作品集《我的宝贝》,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6) 引自三毛与父母的信札,收录于三毛作品集《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