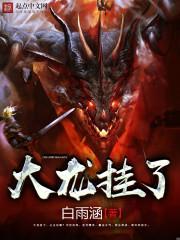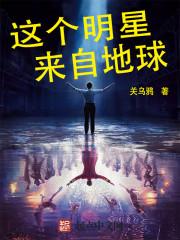奇书网>王阳明三立 > 第三回 苦强求到头终是病劝和尚守仁归正途(第2页)
第三回 苦强求到头终是病劝和尚守仁归正途(第2页)
这又是一句敷衍人的话。
守仁的父亲王实庵老先生状元出身,如今已经官拜礼部右侍郎,很得弘治皇帝器重,将来极有可能入阁拜相。蔡蓬头说王实庵是“第一等人”,这话很多人听了都会服气。偏偏王守仁是个初生牛犊,平时就喜欢做大题、说大话,他哈哈一笑:“依我看读书考功名根本不算大志!”
王守仁为人淳朴真诚,聪明又热情,蔡老道把他当成一个“忘年交”。听守仁说有意思的话,就笑着问:“怎么才算大志?”
听老道士问“大志”,顿时把王守仁已经熄灭过半的雄心勾了起来,仰着脸高声道:“功名利禄只能让人显贵一世,儿子这一辈也还沾点儿光,到了孙子辈就只能说说嘴,之后也就过去了。几百年后谁还会记得?一个读书人,只有明大道,做圣贤,留名千古,才是天下第一等事。”
就这一句话,让蔡老道把手里的茶碗放下了,眼睛也瞪起来了。
——儒生,读圣贤书的儒生!居然有这么大的勇气,敢说自己要“做圣贤”,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
王守仁确实聪明过人,可这世上的聪明人太多,所以单只一份聪明,并没什么了不起。守仁这个人比别人强,就强在他秉性方正、狂放直率,按孔夫子的话说,他这叫作“狂者胸次”。
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意思是说:“我找不到那些道德品行非常完美的人做朋友,就和‘狂者’‘狷者’做朋友吧。‘狂者’就是有大志向、有进取心的人;‘狷者’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他们至少耿直,不会做下流无耻的事。”由此可知,像王守仁这样有志向有勇气的“狂者胸次”是很珍贵、很难得的。
道家虽然讲“出世”,其实和儒家学说有很多相通之处。见王守仁是这么一位难得的“狂者”,蔡老道颇有几分惊喜,一字一句缓缓地说:“你这个‘做圣贤’的志向,好!”
以前王守仁在人前说“做圣贤”总被人笑话,今天蔡蓬头竟然称赞他,顿时喜出望外,忙问:“这么说我真的可以做圣贤?”
蔡老道拿手指头嗒嗒地敲着桌子:“这世上人人皆可做圣贤!你为什么做不得?”
蔡蓬头说的是王守仁一辈子听到的最痛快淋漓的一句话!一时乐得手舞足蹈,赶紧问:“我该怎么做才能成为‘圣贤’?”
听了这一问,蔡蓬头目瞪口呆,连连摇头:“这个我可说不清楚。”
当年王守仁在家里“格竹子”,那时候他既不知何谓“圣贤”,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做圣贤,更不知该如何做圣贤,犯了个“一问三不知”的错儿。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守仁在这件事上毫无长进,当年的“三不知”,现在仍然一条也没弄懂。他忽然提出这么个幼稚的问题,倒把蔡蓬头弄得不知所措。
蔡蓬头已经无话可说,王守仁却还在眼巴巴地等着人家告诉他如何“做圣贤”。见蔡老道不说话了,就急着问:“道长能否多指点些?”
有句话叫作茧自缚,如今的蔡老道真成了“作茧自缚”了。他愁眉苦脸想了半天:“按说你我有缘,应该说几句话给你听。可王大人如今一脸官相,满身贵气,贫道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又低头沉吟半晌,“这样吧,我推荐一个人给你认识:列仙峰旁有个‘毛儿洞’,洞里住着一位‘九柏老人’,你去找他,如果有缘得见,也许对你有帮助。”
听老道士引荐一位异人给自己认识,守仁打从心里笑出声来,赶忙连声称谢,又说:“在下还想和道长盘桓几日。”
“我住在玉清宫,等你从山里回来,可以来找我。”说到这儿,蔡蓬头仔细看了看守仁的脸色,“我看你脸色不好,似乎中气不足。咱们是旧识,有句话说给你听:‘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要知道保养,多处静,少动心思,切忌‘以不足济有余’。”
道士这话说得对。
王守仁自幼生得单薄,身体一直不太好。听蔡蓬头说到这儿,忙问:“依道长之见,在下该如何养命?”
蔡老道微微一笑:“‘养命’谈不到,只是取个‘静’字,少些烦扰吧。贫道今天送你三句话,你记着:‘多学无用,多言无益,多劳无功。’”
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曾有隐士劝他归隐,还有一位“楚狂接舆”狂歌当哭,大呼:“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怠而。”劝孔子退一步,别再受这“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苦。然而孔夫子不听隐士们的劝。
今天蔡老道用“多学无用,多言无益,多劳无功”来劝王守仁,因为这道士看出王守仁耿介忠直,猜到他一生为官命运多舛,所以用这些话来劝他。可惜,王守仁也像当年的孔夫子,根本不听劝!后半辈子,他把老道士说的三项忌讳全都犯了。
说到底,人生道路都是自己走,谁也劝不得谁。
别了蔡蓬头,守仁赶紧向当地人打听“毛儿洞”,结果被问到的人没有一个听说过这个地名。又问“九柏老人”,也只有一两个人隐约知道山里似乎有这么个人,但具体在哪儿谁也说不上来。
守仁是个极有勇气的人,也不管“毛儿洞”在哪儿,先上山再说!可是到了山上再打听,还是没人知道。就这么足足转了两天,问了不知多少人,好不容易有个山民告诉他,荒崖顶上有个无名石洞,洞里住着个“疯子”,吃野果、喝泉水,几年没下过山。
“可那里的山路难走得很,好几处都是断崖绝壁,一个人上去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