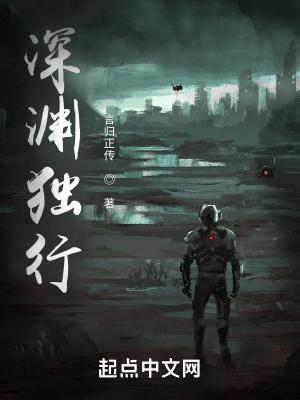奇书网>能人志士 > 二 赵锁柱(第1页)
二 赵锁柱(第1页)
二 赵锁柱
转天一早,我就骑车奔往赵家屯公社的大榆树大队。
这趟路可不算近,也不好走。昨日淋湿的路面,给一夜春寒冻得又硬又滑。我又忘记戴手套,手冷得攥不住车把。再说这种弯弯曲曲累人的乡间土道,在雨天里被沉甸甸的大车轧起一条条棱子,过后又凝结住了,骑车走在上面最危险,我有好几次前轱辘陷进土棱子缝里,差点儿摔得人仰马翻。
进了大榆树大队,找到了赵锁柱家。从他家那用石块和土坯垒成的矮墙上望进去,可以看到一连三间青瓦顶子的规规整整的北房,窗玻璃闪闪发光。院里扫得干干净净,笼罩着墙里墙外几株尚未发芽的大榆树的树影。此刻院里、屋顶、树上,落着一大群麻雀,正吱吱喳喳叫得热闹,反而使这院落显得分外清爽和宁静。我一推开眼前一扇荆条、木杆和粗铁丝编扎的小门,鸟儿“呼啦”一下全都飞跑了。我进了院子,把车子靠在墙边,一边往里走,一边叫着:
“锁柱同志在家吗?”
没人应答。我走到屋门前才发现两扇木板门中间穿挂着一条链子,上了锁头,中间露出一条门缝。他没在家?我扒着门缝往里张望一下,竟使我吃了一惊。我想,任何人见了这情景也会吃惊的。这屋里迎面是张四条腿的八仙桌,对角的两条粗桌腿上竟用麻绳各拴着一个娃娃。显然这就是卓乃丽和赵锁柱的双胞胎儿子!我把嘴对着门缝刚要朝里边喊话,问问他们的爹到哪儿去了,却又停住口。因为我发现这两个娃娃都睡着了。一个倚着桌腿,两条小腿儿曲着,膝盖儿架住垂下来的脑袋;另一个斜卧在地上,面朝着从窗子射进去的暖烘烘的阳光,小脸儿上分明带着哭过和抹过而留下的花花的泪渍。他俩睡得正香甜哪!斜卧在地的这个娃娃打着轻匀的鼾声,从嘴角流淌下来的一道涎水,给阳光照得像蛛丝一样亮。在他们周围乱七八糟地放着盛粥的小碗、小勺、饽饽、山芋、撕碎的纸片和涂得红绿色、一吹就响的小泥猴。这是赵锁柱给孩子们预备的,显然他走了半天,孩子们吃了、玩了、哭了、累了、都睡了……我心里暗暗一揪。虽然我还没见赵锁柱,但眼前的景象已经告诉我他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
我转身刚要去找赵锁柱,只听身后的院门“吱呀”一声。扭头一看,门外走进一个大汉,肩扛着重重一袋粮食。这袋粮食遮住他的面孔。他直朝我这边走来,步子稳健,显得很有力气。
“您就是赵锁柱同志吧?”我问。
他听见我的声音,随即把肩上的重袋子轻轻撂在地上。噢,多魁梧壮实的汉子!高高的个子,厚厚的大手,一身夹棉衣裤也遮盖不住全身肌肉隆起的壮美的形体。他的容貌虽然与英俊无关,不大的微微吊梢的长眼睛,神情有些呆板,方方一张大脸盘上找不到一点儿聪慧伶俐的影子,而且在额头上有一道又长又深的疤痕,但他却有一股憨朴厚实的气息。在北方单调而平静的田野间,人影寥落的村道上,不出名的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农民,就像柳树一样平常。他们好穿黑布衣服,腰间扎一根粗布带子,夏天里大都剃短平头,不爱说话,却很少空着手。不是干点儿什么,就是背着扛着什么重重的东西。他们那憨直的脾气和个性几乎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任何机灵的目光、优雅的风度、文气的举止出现在他们身上,都会显得不调和而马上破坏了他们所特有的气质、破坏了他们固有的美和完整感似的。此刻,他没戴帽子,大概扛着这袋粮食走了不短的路,一缕缕热气从他那又黑又短的头发楂子里冒出来,汗津津的额头闪着光亮。
“俺就是赵锁柱。啥事?”他说。一边拍打肩头上的白色的粉末和碎屑。
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他什么话也没说,只略略皱皱眉头,就提起粮袋,招呼我进屋去坐。当他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门上的锁链时,里边忽然发出一阵哭声。显然是开动锁链的声音吵醒了孩子们。受了委屈的孩子都是用哭来欢迎亲人的。
我俩进了屋,屋里倒是暖烘烘的。赵锁柱叫我上炕去坐。一边忙去解开那捆缚孩子的绳子。放开的孩子就像开笼放出来的小鸡那样快活,又蹦又跳,满屋乱跑。赵锁柱弯腰从灶眼里掏出一块烤得冒着热烟儿的山芋,掰成两半,一个孩子一半,然后说:
“去,当院玩去吧!”
两个模样几乎一样的孩子,用同样胖胖而污黑的小手捧着山芋,带着泪花的小脸儿美滋滋地笑着,随后便一前一后欢叫着跑了出去。那八仙桌的两条桌腿上还都拖着一根不太长的麻绳。
赵锁柱给我斟满热水,也从灶眼儿掏出几块烤熟了的热山芋捧给我吃。在北方农民的家里,主人都是直来直去的,不会客套,实心眼儿,用不着推推让让,说许多没用的客气话。我对这些人的脾气秉性早已习惯,自管动手拿了一块山芋吃起来。再喝几口热水,倒是蛮舒服的。
这时我掏出烟来,让给他一支,他也不客气。不过看他那用食指和拇指捏着纸烟的架势,他是不习惯抽纸烟的。而且,他一捏,就把烟卷捏瘪了。看来他的手挺重。
我同他先扯了几句闲天,然后言归正传。我把昨天与卓乃丽分手后所想到的话全说了。我的目的,是想说服他答应卓乃丽的离婚要求。我认为自己的话说得很有说服力,用词得当,讲得充分,逻辑性又强——我说这些话时,他低头抽烟一声不吭,也毫无反驳我的意思。可是当我谈到:“你们没有共同的感情基础,谈不上来……”他突然头一抬问我:
“啥?啥叫‘基础’?谈个啥?”
这时我看他眉头皱紧一个结结实实的肉疙瘩。顿时我觉得,自己刚才那番煞费苦心、头头是道的劝说全是白搭。听他的问话,说明他根本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你们这种夫妇的精神世界是完全不相通的!”我解释道。其实平常我也不用这种语言与农民谈话,大概是昨天受了卓乃丽那些理论影响太深之故。但赵锁柱听了,睁圆眼睛,好像我说出一句什么怪异惊人的话语。他问我:
“啥?精神世界?”
“精神……”我只得耐心向他说明,使他听懂,“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理想、爱好、趣味、追求……”
“啥?啥?你说的啥呀?!她还要‘求’个啥呀!”他突然叫起来。显然他根本听不懂我的话,却仿佛感到我的话不利于他似的。他有些急了。
他这几个“啥”字却叫我无法再做解释了。事先,我想好的那些话都变得空泛而无力。刹那间,我强烈地感到这两个人——卓乃丽和赵锁柱好像是不同世纪、不同时代、不同天地、不同社会进程的两个人,好像砖块与云彩——它们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结合在一起?这就更使我深信和偏向卓乃丽的离婚理由。一时,不免对这个外表憨朴、内心无知的农民产生一点点儿轻视,不觉说:
“你何必叫她忍受一辈子,痛苦一辈子!你们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