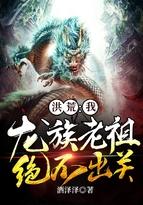奇书网>名人传记 > 米开朗琪罗传002(第3页)
米开朗琪罗传002(第3页)
没有一颗灵魂比米开朗琪罗的更纯洁。没有一个人对于爱情的观念有那么虔敬。
孔迪维曾说:
“我时常听见米开朗琪罗谈起爱情:在场的人都说他的言论全然是柏拉图式的。为我,我不知道柏拉图的主张;但在我和他那么长久那么亲密的交谊中,我在他口中只听到最可尊敬的言语,可以抑灭青年人的强烈的欲火的言语。”
可是这柏拉图式的理想并无文学意味也无冷酷的气象:米开朗琪罗对于一切美的事物,总是狂热的沉溺的,他之于柏拉图式的爱的理想亦是如此。他自己知道这点,故他有一天在谢绝他的友人贾诺蒂的邀请时说:
“当我看见一个具有若干才能或思想的人,或一个为人所不为、言人所不言的人时,我不禁要热恋他,我可以全身托付给他,以至我不再是属于我的了。……你们大家都是那么富有天赋,如果我接受你们的邀请,我将失掉我的自由;你们中每个人都将分割我的一部分。即是跳舞与弹琴的人,如果他们擅长他们的艺术,我亦可听凭他们把我摆布!你们的做伴,不仅不能使我休息、振作、镇静,反将使我的灵魂随风飘零;以至几天之后,我可以不知道死在哪个世界上。”(217)
思想言语声音的美既然如此**他,肉体的美丽将更如何使他依恋呢!
“美貌的力量于我是怎样的刺激啊!
世间更无同等的欢乐了!”(218)
对于这个美妙的外形的大创造家——同时又是有信仰的人——一个美的躯体是神明般的,是蒙着肉的外衣的神的显示。好似摩西之于“热烈的丛树”一般(219),他只颤抖着走近它。他所崇拜的对象于他真是一个偶像,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在他的足前匍匐膜拜;而一个伟人自愿的屈服即是高贵的卡瓦列里也受不了,更何况美貌的偶像往往具有极庸俗的灵魂,如波焦呢!但米开朗琪罗什么也看不见……他真正什么也看不见吗?——他是什么也不愿看见;他要在他的心中把已经勾就轮廓的偶像雕塑完成。
他最早的理想的爱人,他最早的生动的美梦,是一五二二年的佩里尼(220)。一五三三年他又恋着波焦;一五四四年恋着布拉奇(221)。因此,他对于卡瓦列里的友谊并非专一的;但确是持久而达到狂热的境界的,不独这位朋友的美姿值得他那么颠倒,即是他的德行的高尚也值得他如此尊重。
瓦萨里曾言:“他爱卡瓦列里甚于一切别的朋友。这是一个生在罗马的中产者,年纪很轻,热爱艺术;米开朗琪罗为他做过一个肖像——是米氏一生唯一的画像;因为他痛恨描画生人,除非这人是美丽无比的时候。”(222)
瓦尔基又说:“我在罗马遇到卡瓦列里先生时,他不独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美貌,而且举止谈吐亦是温文尔雅,思想出众,行动高尚,的确值得人家的爱慕,尤其是当人们认识他更透彻的时候。”
米开朗琪罗于一五三二年秋在罗马遇见他。他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充满了热情的诉白,卡瓦列里的复信(223)亦是十分尊严:
我收到你的来信,使我十分快慰,尤其因为它是出乎我意外的缘故;我说:出乎我意外,因为我不相信值得像你这样的人写信给我。至于称赞我的话,和你对于我的工作表示极为钦佩的话,我可回答你:我的为人与工作,绝不能令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如你一般的人——我说举世无双,因为我不信你之外更有第二个——对一个启蒙时代的青年说出那样的话。可是我亦不相信你对我说谎。我相信,是的,我确信你对于我的感情,确是像你那样一个艺术的化身者,对于一切献身艺术爱艺术的人所必然地感到的。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而在爱艺术这一点上,我确是不让任何人。我回报你的盛情,我应允你:我从未如爱你一般地爱过别人,我从没有如希冀你的友谊一般希冀别人……我请你在我可以为你效劳的时候驱使我,我永远为你驰驱。
你的忠诚的托马索·卡瓦列里
卡瓦列里似乎永远保持着这感动的但是谨慎的语气。他直到米开朗琪罗临终的时候一直对他是忠诚的,他并且在场送终。米开朗琪罗也永远信任他;他是被认为唯一的影响米开朗琪罗的人,他亦利用了这信心与影响为米氏的幸福与伟大服役。是他使米开朗琪罗决定完成圣彼得大寺穹隆的木雕模型。是他为我们保留下米开朗琪罗为穹隆构造所装的图样,是他努力把它实现。而且亦是他,在米开朗琪罗死后,依着他亡友的意志监督工程的实施。
但米开朗琪罗对他的友谊无异于爱情的疯狂。他写给他无数激动的信。他是俯伏在泥尘里向偶像申诉(224)。他称他“一个有力的天才……一件灵迹……时代的光明”;他哀求他“不要轻蔑他,因为他不能和他相比,没有人可和他对等”。他把他的现在与未来一起赠给他;他更说:“这于我是一件无穷的痛苦:我不能把我的已往也赠予你以使我能服侍你更长久,因为未来是短促的:我太老了……”(225)“我相信没有东西可以毁坏我们的友谊,虽然我出言僭越;因为我还在你之下。”(226)“……我可以忘记你的名字如忘记我借以生存的食粮一般;是的,我比较更能忘记毫无乐趣地支持我肉体的食粮,而不能忘记支持我灵魂与肉体的你的名字……它使我感到那样甘美甜蜜,以至我在想起你的时间内,我不感到痛苦,也不畏惧死。”(227)“——我的灵魂完全处在我把它给予的人的手中……”(228)“如我必得停止思念他,我信我立刻会死。”(229)
他赠给卡瓦列里最精美的礼物:
“可惊的素描,以红黑铅笔画的头像,他在教他学习素描的用意中绘成的。其次,他送给他一座《被宙斯的翅翼举起的甘尼米》,一座《提提厄斯》和其他不少最完美的作品。”(230)
他也寄赠他十四行诗,有时是极美的,往往是暗晦的,其中的一部分,不久便在文学团体中有人背诵了,整个意大利都吟咏着(231)。人家说下面一首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最美的抒情诗”:谢拂莱尔言。
“由你的慧眼,我看到为我的盲目不能看到的光明。你的足助我担荷重负,为我疲痿的足所不能支撑的。由你的精神,我感到往天上飞升。我的意志全包括在你的意志中。我的思想在你的心中形成,我的言语在你喘息中吐露。孤独的时候,我如月亮一般,只有在太阳照射它时才能见到。”(232)
另外一首更著名的十四行诗,是颂赞完美友谊的最美歌词:
“如果两个爱人中间存在着贞洁的爱情,高超的虔敬,同等的命运,如果残酷的命运打击一个时也同时打击别个,如果一种精神一种意志统治着两颗心,如果两个肉体上的一颗灵魂成为永恒,把两个以同一翅翼挟带上天,如果爱神在一支箭上同时射中了两个人的心,如果大家相爱,如果大家不自爱,如果两人希冀他们的快乐与幸福得有同样的终局,如果千万的爱情不能及他们的爱情的百分之一,那么一个怨恨的动作会不会永远割裂了他们的关联?”诗集卷四十四。
“我哭,我燃烧,我磨难自己,我的心痛苦死了……”(233)
他又和卡瓦列里说:“你把我生的欢乐带走了。”(234)
对于这些过于热烈的诗,“温和的被爱的主”(235)卡瓦列里却报以冷静的安定的感情(236)。这种友谊的夸张使他暗中难堪。米开朗琪罗求他宽恕:
“我亲爱的主,你不要为我的爱情愤怒,这爱情完全是奉献给你最好的德行的;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应当爱慕别个人的精神。我所愿欲的,我在你美丽的姿容上所获得的,绝非常人所能了解的。谁要懂得它应当先认识死。”(237)
当然,这爱美的热情只有诚实的份儿。可是这热烈的惶乱(238)而贞洁的爱情的对象,全不露出癫狂与不安的情态。
在这些心力交瘁的年月之后——绝望地努力要否定他的生命的虚无而重创出他渴求的爱——幸而有一个女人的淡泊的感情来抚慰他,她了解这孤独地迷失在世界上的老孩子,在这苦闷欲死的心魂中,她重新灌注入若干平和、信心、理智和凄凉地接受生与死的准备。
一五三三年与一五三四年间(239),一五三五年,他开始认识维多利亚·科隆娜。
她生于一四九二年。她的父亲叫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是帕利阿诺地方的诸侯,塔利亚科佐亲王。她的母亲,阿涅斯·特·蒙泰费尔特罗,便是乌尔比诺亲王的女儿。她的门第是意大利最高贵的门第之一,亦是受着文艺复兴精神的熏沐最深切的一族。十七岁时,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大将军弗朗切斯科·特·阿瓦洛。她爱他;他却不爱她。她是不美的(240)。人们在小型浮雕像上所看到的她的面貌是男性的,意志坚强的,严峻的:额角很高,鼻子很长很直,上唇较短,下唇微向前突,嘴巴紧闭。认识她而为她作传的菲洛尼科·阿利尔卡纳塞奥虽然措辞婉约,但口气中也露出她是丑陋的:“当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的时候,她正努力发展她的思想;因为她没有美貌,她修养文学,以获得这不朽的美,不像会消逝的其他的美一样。”——她是对于灵智的事物抱有热情的女子。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说“粗俗的感官,不能形成一种和谐以产生高贵心灵的纯洁的爱,它们绝不能引起她的快乐与痛苦……鲜明的火焰,把我的心升华到那么崇高,以至卑下的思想会使它难堪”。——实在是她在任何方面也不配受那豪放而纵欲的佩斯卡拉的爱的;然而,爱的盲目竟要她爱他,为他痛苦。
她的丈夫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欺骗她,闹得整个那不勒斯都知道,她为此感到残酷的痛苦。可是,当他在一五二五年死去时,她亦并不觉得安慰。她遁入宗教,赋诗自遣。她过着修道院生活,先在罗马,继而在那不勒斯(241),但她早先并没完全脱离社会的意思:她的寻求孤独只是要完全沉浸入她的爱的回忆中,为她在诗中歌咏的。她和意大利的一切大作家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等都有来往,卡斯蒂廖内把著作《侍臣论》托付给她,阿里奥斯托在他的《疯狂的奥兰多》中称颂她。一五三〇年,她的十四行诗流传于整个意大利,在当时女作家中获得一个唯一的光荣的地位。隐在伊斯基亚荒岛上,她在和谐的海中不绝地歌唱她的蜕变的爱情。
“基督的法律是自由的法律……凡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不能称为政府;因为它在原质上便倾向于恶而且受着无数情欲的拨弄。不!一切主宰是理智的主宰。他的目的在以正当的途径引领一切服从他的人到达他们正当的目的:幸福。教皇的权威也是一种理智的权威。一个教皇应该知道他的权威是施用于自由人的。他不应该依了他的意念而指挥,或禁止,或豁免,但应该只依了理智的规律、神明的命令、爱的原则而行事。”
维多利亚,是联合着全意大利最精纯的意识的这一组理想主义中的一员。她和勒内·特·费拉雷与玛格丽特·特·纳瓦雷们通信;以后变成新教徒的皮耶尔·保罗·韦尔杰廖称她为“一道真理的光”。——但当残忍的卡拉法(247)所主持的反改革运动开始时,她堕入可怕的怀疑中去了。她是,如米开朗琪罗一样,一颗热烈而又怯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不能抗拒教会的权威。“她持斋、绝食、苦修,以致她筋骨之外只包裹着一层皮。”(248)她的朋友,波莱主教(249)叫她抑制她的智慧的骄傲,因了神而忘掉她自己的存在:这样她才稍稍重新觅得平和。她用了牺牲的精神做这一切……然而她还不止牺牲她自己!她还牺牲和她一起的朋友,她牺牲奥基诺,把他的文字送到罗马的裁判异教徒机关中去;如米开朗琪罗一般,这伟大的心灵为恐惧所震破了。她把她良心的责备掩藏在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中:
“你看到我处在愚昧的混沌中,迷失在错误的陷阵里,肉体永远劳动着要寻觅休息,灵魂永远骚乱着找求平和。神要我知道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要我知道一切只在基督身上。”(250)
她要求死,如要求一种解放。——一五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死了。
在她受着瓦尔德斯与奥基诺的神秘主义熏染最深的时代,她认识了米开朗琪罗。这女子,悲哀的、烦闷的,永远需要有人做她的依傍,同时也永远需要一个比她更弱更不幸的人,使她可以在他身上发泄她心中洋溢着的母爱。她在米开朗琪罗前面掩藏着她的惶乱。外表很宁静、拘谨,她把自己所要求之于他人的平和,传递给米开朗琪罗。他们的友谊始于一五三五年,到了一五三八年渐趋亲密,可完全建筑在神的领域内。维多利亚四十六岁,他六十三岁。她住在罗马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道院中,在平乔山冈之下。米开朗琪罗住在卡瓦洛岗附近。每逢星期日,他们在卡瓦洛岗的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中聚会。修士阿姆布罗焦·卡泰里诺·波利蒂诵读《圣保罗福音》,他们共同讨论着。葡萄牙画家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在他的四部绘画随录中,曾把这些情景留下真切的回忆。在他的记载中,将严肃而又温柔的友谊描写得非常动人。
“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一定更爱听米开朗琪罗的谈话。”
弗朗西斯科被这句话中伤了,答道:
“怎么,夫人,你以为我只有绘画方面的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