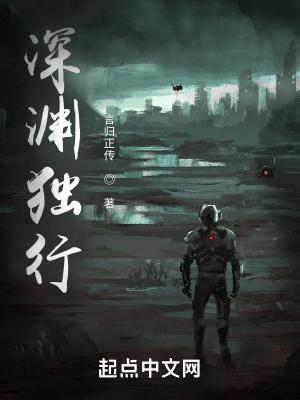奇书网>绕着地球转一圈是多少公里 > 东南亚明珠(第2页)
东南亚明珠(第2页)
遍布各个角落的小贩中心生意极好,从早到晚人来人往。这里最普遍的生意就是各种小吃,不但能吃到很多市面上难以见到的地道小吃,而且价格也极其公道。一碗鲜虾面的价格不到四新元,大约合人民币20元。
在牛车水附近的一个小贩中心里,因为避雨而与开小吃店的大嫂聊了起来。她的小铺子是整个小贩中心里位置最好的一间,面积不足六平方米,每月的租金800新元,这点租金实际上还不足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多。因为没有什么租金压力,所以夫妇俩也不大肯耗费太多的时间在这间小铺上,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就收工回家。不过据大嫂介绍,也有一些店主为了挣到更多的钱而辛苦到半夜一两点钟。
在这里,我意外地发现做勤杂工的几乎全都是年长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没学历二没精力,在就业市场上不具备太强的竞争力,而小贩中心的大量存在,刚好为这群人提供了自谋生路以及再就业的机会。
小贩中心不仅在扩大群众就业上起着很好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调节市场物价的作用。其低廉的价格一下子就拉低了新加坡整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对于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及外籍劳工来说,小贩中心简直就是消费天堂,实际上即便是拥有较高收入的城市白领也乐于在这里解决一日三餐。
据说,因为在小贩中心里吃饭实在便宜,以至于大部分新加坡人的家里都已经懒得开伙做饭了。一份两荤两素的盖浇饭最低价格只有2。5新元(约合人民币13元),一杯咖啡或奶茶的价格基本上也都在一新元左右。对于这样的价格,不仅新加坡人感到便宜,连我这样的旅游者都觉得划算。有人开玩笑地说,新加坡无处不在的小贩中心对于解决该国的民生问题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呢。
新加坡的烂货市场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既有一掷千金的富人,也不乏手头拮据的劳苦大众。否则就不会有这个颇具规模的烂货市场的存在。市场里卖的东西可说是五花八门,尤以售卖二手服装和鞋帽的摊位为多。
有些新加坡汉语也让人误会
绝大多数时候,新加坡人讲的汉语与中国大陆人讲的没有什么不同,就连两地的汉语拼音也完全相同,但还是有个别词汇在语意上存在着细微差别,却很容易引起误会。
刚到新加坡那天,在长途汽车站下车后,我们便询问工作人员到预定的旅馆怎么走。工作人员接过英文地图和详细地址看了看,说:“不懂。”我又把地图和地址递给第二个人,也告诉我“不懂”,建议我还是打“德”去为好。虽然是第一次听到打“德”的说法,但还是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让我乘坐出租车过去。原来新加坡人管出租车叫做“德士”。
本以为新加坡人的英文水平都还可以,却怎么都搞不懂那小小的英文地图呢?后来才知道,这恰恰是因为语言差异造成的误会。
打上出租车,司机一张口就引起了我小小的不快——他用批评的口吻问我:“旅馆在哪里你自己不懂吗?”我老实地回答:“不懂。”一边回答一边再次拿出地图让司机看,没想到司机连头也没回就说了句:“你不懂新加坡的法律,这里不让一边开车一边看地图……”这个司机一口一个“你不懂”,让我这个掏钱坐车的乘客心里多少涌出了不快。
到新加坡的第二天早上,我去街边的一家小超市买报纸,店主让我自己去门口的架子上取。到门口一看,根本就没有什么报纸,于是又走进店里告诉老板。这时候,店主略带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不懂,本以为架子上还有报纸。”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新加坡人嘴里的“不懂”其实是“不知道”的意思啊!
当天在报纸上又看到一个“不懂”的中文词汇:罗里。某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罗里司机”,看着这几个能读会认的中国字,却怎么也搞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还是在旅馆老板那里得到了确切答案:所谓“罗里”,其实就是“货车”的意思。
此外,和新加坡人聊天的时候很容易听到另外一个新词:伯仙。当我询问当地华人在人口构成中的比例时,他们回答说大概有七八十伯仙。乍一听还真不大懂,刚要询问,忽然意识到,那不就是百分比的英文音译吗?
其实,新加坡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中文歧义词,譬如说我们在喝汽水的时候喜欢用吸管,而新加坡人则管吸管叫“水草”,这些歧义词有的令人感觉新鲜,而有的又有可能会引起小小的误会。好在这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更是一个提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时代,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歧义词,如若能做到既知己又知彼,那什么样的文化差异不能够克服呢?
马来西亚华人真热情
在吉隆坡找旅馆的过程既艰难又轻松。
起初,面对复杂的街巷以及艰涩的地名实在有些困惑。不过中国人在这里还是很容易得到帮助的,据说华人在吉隆坡的人口构成中所占比例几乎超过了30%。
在寻找旅馆的时候,一位过路的华人老大哥不仅详细地给我们指了路,甚至停在街边看着我们走远,发现我们拐错了方向,又马上追过来为我们纠正。这位老大哥虽然从没有到过中国,和我们聊起中国来居然滔滔不绝,他说不久前刚刚看过亚运会的开幕式,本以为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建得不错,没想到广州也是那么漂亮。
巧的是旅馆的前台接待也是一位华人,她准备春节一过就去北京旅行,想看看奥运会后的北京是什么样。在吉隆坡停留一晚后,我们计划先到新加坡去玩几天,为了第二天能够顺利一些,我们决定提前去探路。
在一家华人开的小店里,店主的女儿告诉我们,吉隆坡的长途汽车站已经搬到别的地方了。虽然有些难找,但初来乍到的我们还是还是决定自己找过去。
路过一个华文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华人大哥不仅热情地为我们指路,甚至还想用他的摩托车送我们过去。考虑到他只有一辆摩托车,我只有婉言谢绝了。不过在这位大哥的耐心指导下,我们终于乘上了“空中火车”。车厢里偶遇两个华人青年,又告诉我们去汽车总站还要换乘一种叫LRT的轻轨列车。于是,我们又换乘了这种地上轻轨列车,并最终到达了位于市郊的汽车总站。
大宝森节
印度教的“大宝森节”(Thaipusam)大多落在每年公历的1、2月间,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赎罪、奉献及感恩的时节。据说在印度本土已经看不到了,现在依旧保留这个风俗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和其他具有欢乐气氛的印度节日不同,大宝森节是个忏悔和实践诺言的节日。
信徒的祭祀仪式有很多种,例如:剃头,做法事,用银针刺穿舌头、双颊等,其中最突出的方法就是背部肉体上嵌入无数个铮亮的小铁钩,这些铁钩类似鱼钩,每个钩尾都结着一条粗绳子,由后面一人集中抓在左手,牵拉扯紧,同时右手挥舞着一条鞭子不停地鞭打驱赶前面的教徒。有的教徒则在每一个铁钩上沉沉地坠满苹果、茶壶之类的物品,或是背着巨大的钢制弓形枷锁(负卡瓦第),从一座印度神庙游行到另一座印度神庙,进行祷告及献祭,借此表示对神明忠贞不移的信仰,并祈求神明的赐福。
巴厘岛:农家乐的最高境界
巴厘岛,被无数旅行者称为“第一度假天堂”。
度假天堂,当然少不了豪华的星级酒店。但阳光沙滩与高级酒店,都只是使之成为度假天堂的必要条件之一,巴厘岛的魅力不在于此。
巴厘岛的特殊之处,也并非古迹,比巴厘岛历史更为悠久,文化更为璀璨的文化遗迹世界上还有很多。和许多“驴友”一样,我关注的是巴厘岛的“农家乐”。
我在巴厘岛住的第一家旅馆就是农民的房子,虽说是农家院,难得的是,环境既不简陋粗糙,又不至于艳俗。
这户人家在餐厅周围挖了一个不太深的人工水池,池子里放养着各种鱼类,偶尔还有青蛙跳出来唱上几句。餐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围墙,房子周围是一圈丰茂的热带植物,置身其中,真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旅馆的小二楼一共有八间客房,所有的阳台都正对着一片开阔的农田。一截矮墙把院子与农田分隔开来,矮墙的高度刚刚好,客人即便是坐下来也能够欣赏到农夫耕作的田园景象。我租住的是位于一楼的一套标准间,里面设有独立的洗手间和淋浴房,入住一晚价格大约是160元人民币,还包括一顿地道的英式早餐。
许是见得太多,田里的农民对游客的镜头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左拍右拍丝毫影响不了他们劳作的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