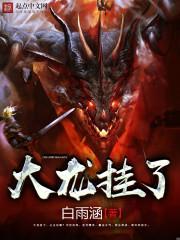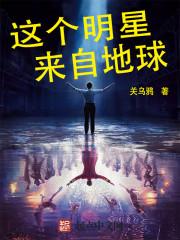奇书网>弗洛伊德文章 > 自我与本我03(第1页)
自我与本我03(第1页)
自我与本我03
对正常的、有意识的罪疚感(良心)进行解释并没有什么困难;它是以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为基础的,并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进行自我谴责的表现。可以推测,神经症中如此熟知的自卑感(thefeelingsofiy)可能和这种有意识的罪疚感密切相关。在两种非常熟悉的疾病中,罪疚感被过分强烈地意识到;自我理想在其中表现得特别严厉,常常极其残暴地对自我大发雷霆。自我理想在这两种疾病(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中的态度,和这种类似性一道,表现出具有同样意义的差异。
在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罪疚感竭力表现自己,但又不能向自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这种病人的自我反对转嫁罪责,并在否定它的同时寻求医生的支持。对此予以默认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分析最终表明,超我正受着自我所不知道的过程的影响。要想发现真正位于罪疚感根基的被压抑的冲动是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的本我。
在抑郁症中,超我获得了对意识的控制,这种印象甚至更加强烈。但在这种病例中,自我不敢贸然反抗;它承认有罪并甘愿受罚。我们理解这种差异。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问题在于,应受斥责的冲动从未形成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抑郁症中,超我向其表达愤怒的对象则通过认同作用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罪疚感能在这两种神经症中达到如此非凡的强度;但是,这种事态所表现的主要问题在于另一方面。在我们处理了其他病例之后再来讨论它——在这些其他病例中,罪疚感始终是潜意识的。
在癔症和某种癔症状态下,基本的条件就是发现这种罪疚感。罪疚感用以保持潜意识的机制是容易发现的。癔症的自我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知觉,它的超我的批判正是以此来威胁它,要采取那种保护自己免受无法忍受的对象-贯注的同样方式,也就是采取一种压抑行为。因此,正是自我应该对这种保留在潜意识中的罪疚感负责。我们知道,一般来说,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进行压抑的;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它把同样的武器转而对准它的严厉的监工了。在强迫性神经症里,如我们所知,反向作用的现象占主导地位;但是(癔症中的)自我在这里却满足于和罪疚感所涉及的材料保持距离。
人们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大部分罪疚感在正常情况下必定是潜意识的,因为良心的根源和属于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紧密相连。如果有人想提出这种矛盾的假设,即正常的人不仅远比他所相信的更不道德,而且也远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那么,该论断的前半句是以精神分析的发现为依据的,精神分析对剩下的那后半句则不反对人们提出异议。[237]
这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加剧会使人成为罪犯,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但无疑却是个事实。在许多罪犯中,特别是年轻的罪犯中,会发现他们在犯罪之前就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罪疚感。因此,罪疚感不是它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就好像能把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施加到某种真实的和直接的东西上就是一种宽慰。[238]
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超我表现出它和意识的自我无关,而和潜意识的本我却有密切关系。现在关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把它归之于自我中的前意识字词记忆痕迹,于是,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了,超我,假如它是潜意识的,它是否还能存在于这种字词表象中,或者假如不是潜意识的,它究竟存在于何处呢?我们暂时的回答是超我和自我一样,都不可能否认它是从听觉印象中起源的;因为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字词表象(概念、抽象作用)而和意识相通。但是,这种贯注的能量(catheergy)并未到达起源于听知觉(教学、读书等)的超我的这些内容,而是触及了起源于本我的超我的这些内容。
我们放在后面回答的那个问题就是:超我是怎样主要作为一种罪疚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批评——因为罪疚感是在自我中对这种批评做出回答的知觉)来表示自己,另外,是怎样发展到这样对自我特别粗暴和严厉的呢?如果我们先转向抑郁症,就会发现,对意识获得支配权的特别强烈的超我对自我大发雷霆,好像它要竭尽全力对这个人施虐。按照我们关于施虐狂的观点,我们应该说,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之中,并转而反对自我。现在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可以说是对死的本能的一种纯粹的培养。事实上,假如自我不及时地通过转变成躁狂症以免受其暴政统治的话,死的本能就常常成功地驱使自我走向死亡。
以某种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进行的良心的谴责也同样是令人痛苦和烦恼的。但对这里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相反,它决不采取自我毁灭的步骤;好像它能避免自杀的危险,而且比癔症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除危险,我们能够发现,保证自我的安全的东西就是保留了对象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向前**组织的退行,就能使爱的冲动转变成对对象的攻击冲动。破坏性本能在这里再次得到释放,其目的在于毁灭对象,或至少看起来具有这个意图。这些目的尚未被自我采纳;自我用反相作用和预防措施来奋力反对这种意图,而这些意图就保留在本我中。但是,超我的表现却好像是说,自我应该为此负责,并且在惩罚这些破坏性意图时,用它的严肃性表明,它们不但是由退行引起的伪装,而且实际上用恨代替了爱。由于两方面都孤立无援,自我同样徒劳地防御凶恶的本我的煽动、防御对实施惩罚的良心进行责备。但它至少成功地控制了这两方面的最残忍的行动;第一个结果是没完没了的自我折磨,最后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对对象做系统的折磨。
它们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个人机体内危险的死的本能的活动,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和性成分的融合而被描绘成无害的,另一部分以攻击的形式掉过头来朝向外部世界,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无疑继续畅行无阻地从事它们的内部工作。那么,在抑郁症中超我是怎样成为死的本能的一个集结点的呢?
从本能控制观和道德观来看,或许可以说本我完全是非道德的,自我则力争成为道德的,而超我则可能是超道德的,因此才能变得像本我那样冷酷无情。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越是控制它对别人的攻击性倾向,他在其自我理想中就越残暴——也就是越有攻击性。而日常的观点对这种情况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自我理想所建立的标准似乎成为压制攻击性的动机。但是,我们前面说过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越控制它的攻击性,它的自我理想对其自我的攻击性倾向就越强烈。[239]这就像是一种移置作用,一种向其自我的转向,即便是普通正常的道德品行也有一种严厉限制、残酷禁止的性质。的确,无情地实施惩罚的那个更高级的存在的概念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若不引入一个新的假设,我就无法继续考虑这些问题。如我们所知,超我产生于把父亲作为榜样的一种认同作用。每一种这类认同作用本质上都是失性欲化的,甚或是升华了的。现在看来,好像当这种转变发生时,同时会出现一种本能的调离。升华之后,性成分再也没有力量把以前和它结合的全部破坏性成分都结合起来,这些成分以倾向于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形式被释放。这种解离就是被理想——它的独裁的“你必须……”(Thoushalt)——所展示的普遍严厉性和残酷性的根源。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强迫性神经症。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把爱变成攻击性虽未受到自我力量的影响,却是在本我中产生的一种攻击性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已超出本我,而扩展到了超我,超我现在加强了对清白的自我的残暴统治。但是,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和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一样,自我通过认同作用获得了对力比多的控制,但这样做便受到了超我的惩罚,超我是用以前曾和力比多混合在一起的攻击性来惩罚自我的。
我们关于自我的观点开始趋向于清晰,它的各种关系也变得日渐明白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自我的力量和弱点。它起着重要的作用。自我依靠它和知觉系统的关系而以时序来安排心理过程,使它们服从于“现实检验”。[241]通过插入这种思维过程,自我就能保证动力释放的延迟,并控制着运动的通路[240],当然,这后一种力量与其说是事实问题,不如说是形式问题,就行动而论,自我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的地位一样,没有他的批准,什么法律也无法通过;但是,他对国会提出的任何议案行使否决权以前,早就犹豫不决。起源于外部的一切生活经验丰富了自我;但是,本我对它来说则是另一个外部世界。自我力图使本我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它把力比多从本我中撤回,并把本我的对象-贯注转变成自我结构。在超我的帮助下,是以我们还不清楚的方式,它利用了贮藏在本我中的过去时代的经验。
本我的内容借以深入自我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的,另一条是借助于自我理想的引导;对某些心理活动来说,这两条道路中它们采纳哪一条可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自我从接受本能发展到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发展到抑制它们。在这个成就中,自我理想承担了很大一份,的确,它部分地是反对本我的那种本能过程的一种反相作用。精神分析是使自我把它对本我的统治更推进一步的一个工具。
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把这同一个自我看作是受三个主人的支使,因此便受到三种不同危险威胁的一个可怜的家伙:这三种危险分别来自外界,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和来自超我的严厉性。因为焦虑是一种退出危险的表示,因此,就有和这三种危险相对应的三种焦虑。就像居住在边疆的人一样,自我试图做世界和本我之间的媒介,它要使本我遵照世界的愿望去做,并通过肌肉的活动,使世界顺从本我的愿望。实际上他的行为就像用精神分析进行治疗的医生一样,由于它注重现实世界的力量,而把自己作为一个力比多对象提供给本我,目的在于使本我的力比多依附于它自己。它不仅是本我的一个助手,而且是向主人讨喜的一个顺从的奴隶。只要有可能,自我就试图和本我友好相处;它用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把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盖起来;甚至当它事实上保持冷酷无情时,它也假装出本我对现实的命令表示顺从,它给本我和现实的冲突披上了伪装;如若可能,它也会给和超我的冲突披上伪装。自我在本我和现实之间的地位使它经常变成献媚的,机会主义和假惺惺的,就像一个政客,虽然看见了真理,却又想保持他的受大众拥戴的地位。
自我对两类本能的态度并不是公正的。通过它的认同作用和升华作用,对本我的死的本能掌握力比多是个帮助,但这样做会给它带来成为死的本能的对象和灭亡自己的危险。为了能以这种方式给以帮助,它只好用力比多来充斥自身,这样,它本身就成为爱欲的代表,并且从那时起就渴望活下去和被人所爱。
但是,由于自我的升华作用导致对本能的解离和攻击性本能的超我中的解放,自我对力比多的斗争则面临着受虐待和死亡的危险。在受到超我的攻击之苦,甚至屈从于这些攻击的情况下,自我所遭受的命运就像原生动物被自己创造的裂变物所毁灭一样。[242]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在超我中起作用的道德品行似乎是一种类似的裂变物。
在自我所处的这种从属关系中,它和超我的关系或许是最有趣的。
自我是焦虑的真正住所。[243]由于受到三方面的威胁,自我通过从危险知觉或从本我的同样危险的过程中收回自己的精神贯注,并把它作为焦虑排放出来,从而使逃避反射(flight-reflex)得到发展。后来由于引入了保护性贯注(恐怖症的机制),而取代了这个原始的反应。自我所害怕的东西,不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力比多的危险,我们都无法详加说明;我们只知道这种害怕具有推翻和消灭的性质,但无法用精神分析来把握。[245]自我只是服从快乐原则的警告。另一方面,我们还能说明,在自我害怕超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我害怕的是良心。[244]后来成为自我理想的更优越的存在曾用阉割来威胁自我,这种对阉割的恐惧可能就是后来对良心的恐惧所聚焦的核心;正是这种对阉割的恐惧才作为良心的恐惧而保留下来。
“每一种恐惧最终都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言过其实的警句几乎毫无意义,而且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证明是合理的。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把害怕死亡和害怕外界对象(现实性焦虑)及神经症的力比多焦虑区分开来才是完全正确的。这给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死亡是一个具有消极内容的抽象概念,对此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潜意识有关的东西。看来害怕死亡的只能是,自我大量放弃它的自恋力比多贯注,也就是放弃它自己,正如在另一些使它感觉焦虑的情况下,自我放弃某个外部对象那样,我相信对死亡的恐惧是发生在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某种东西。
我们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两种情况和其他各种焦虑得到发展的情境完全相似),这就是说,是一种对外部危险的反应和一种内部过程,例如像在抑郁症中那样。神经症的表现形式可以再次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