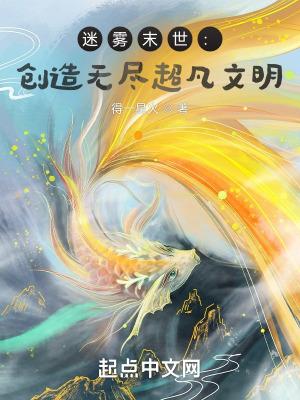奇书网>民俗从傩戏班子开始全本 > 第234章杀神23(第1页)
第234章杀神23(第1页)
诸般种种手段,吴峰已经从“自给自足”之中,再上一层楼。
到达了“布施至下”。
只不过暂时,吴峰没有将这个“人道巫术”传给了师父和师公,猪儿和狗儿的打算。
“青帝法”的根源,就在吴峰的。。。
风铃响过三声,便戛然而止。
禾苗闭上眼,手指轻轻抚过石墙上那些深深浅浅的名字。指尖划过“林朔”二字时,她顿了顿,仿佛触到了一缕尚存余温的气息。阳光斜照在启音井的边缘,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地底的路,又像一根连接生死的线。
那天之后,井口再未闭合。
藏名堂的阶梯虽已隐去,但每隔七日,井壁便会微微震颤,蓝莲花从石缝中钻出,一朵、两朵,不多不少,正好十二朵??那是守语残脉归位的数目。人们说,这是他们在呼吸;禾苗知道,这是他们在说话。
她不再教孩子吹稻草笛了。
不是不愿,而是不必。如今的孩子生来就会。他们张嘴哼出的第一句调子,往往是某段失传百年的傩戏唱腔,或是早已无人使用的古羌语祷词。语言像种子,在沉默中蛰伏千年,只待一声呼唤,便破土而出。
阿芽还住在井边。
她已不再是那个脸蛋红扑扑、吹不响笛子的小女孩。十六岁的她个子高挑,眼神清澈,手里总捧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她从梦中听来的句子。她说,每夜入睡,外公韦明德都会坐在她床前,一页页翻动那本《布洛陀经诗》,用壮话低声诵读。她不懂其中含义,却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
学者们来了又走。
有人想带她去北京做研究,说她的大脑可能具备某种“跨代记忆遗传”的特质;有人称她是“活态非遗载体”,建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更有国外机构匿名开出天价,想买断她所记录的所有内容。
阿芽全都摇头。
“这不是我的东西。”她说,“是外公还回来的债。”
她在井边搭了个小棚子,白天教孩子们写壮文,晚上则点起油灯,一笔一画誊抄那些梦中得来的文字。纸不够用了,就用烧过的木炭在石板上写;墨迹模糊了,就用雨水化开蓝莲花的汁液当墨水。渐渐地,竟整理出整整三卷残篇,虽不连贯,却与考古发现的零星竹简高度吻合。
一位广西民族大学的老教授跪在她面前,老泪纵横:“我们找了一辈子……原来它一直没死,只是睡着了。”
冬至那天,启音井迎来了最盛大的一次还名仪式。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与者挤满了山谷。有戴白帽的回族老人,捧着一本手抄的《突厥语大辞典》残卷;有藏族妇女,将祖母临终前口述的创世史诗录成磁带,放入羊皮囊沉入井中;还有几位聋哑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用手语“朗诵”一段段被遗忘的民谣??他们的手势整齐划一,如风吹麦浪,在空中划出无形的韵律。
就在午夜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井面忽然沸腾。
不是水花四溅的那种沸腾,而是一种内在的震动,仿佛整口井成了一口巨大的共鸣箱。紧接着,十二道光柱自井底冲天而起,直贯云霄,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每一束光中,都浮现出一个名字:
**周培元**
**沈昭华**
**乌力吉?巴特尔**
**陈十四娘**
**韦明德**
**李砚舟(噪音公社创始人)**
**赵玉梅(西南某村最后一位女鬼师)**
**王大耳(东北跑单帮说书人)**
**阿?(傣族贝叶经守护者)**
**韩十三(西北秦腔盲艺人)**
**欧志宏(闽南讲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