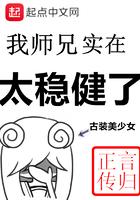奇书网>全家流放到海南免费 > 第一百七十七章 望舒小筑(第1页)
第一百七十七章 望舒小筑(第1页)
马车驶入嘉州镇时,阳光正斜斜地切过城楼的飞檐。青石板被车轮碾过,石板之中的缝隙里钻出几株倔强的野草。有一株野豌豆,顶着嫩绿的芽,在风里轻颤。官道两旁酒旗招展,不时有着小贩的吆喝声。卖豆花的妇人拿着铜勺,一勺一勺地舀着豆花。卖饴糖的老人敲着铜锣,“咚咚咚”,却在巷口处拐了个弯。洛曦宁隔着窗帘,指尖微微收紧。她本以为自己会看见一间局促的小铺,斑驳的木板门,褪色的幌子,大伯母站在灶台前,袖口处满是补丁,就像是所有苦苦支撑着日子的妇人那般。她甚至想过,自己该如何才能不损大伯母的颜面。是先叹口气,再握住大伯母的手,说一句“原谅宁宁来迟”,还是却不想,眼前的场景让那句叹息在喉咙里转了一个圈,化作了一个极轻的“咦”字。隔着窗帘,远远便瞧见了望舒小筑。有些出乎她的意料,望舒小筑的格局并非她印象中那般的憋屈。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紫藤,并非记忆中稀稀疏疏的几串,而是一条壮阔的紫色瀑布,从青瓦上倾泻而下,花序甚至密得看不见叶子。洛曦宁有些疑惑,此处温度虽然不高,可是这紫藤为何能开得如此茂盛,这花也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紫色,而是带着一种淡淡的紫金色。院墙也并不高,却极为精巧。青砖磨得发亮,砖缝以白灰勾出如意纹。马车停在院门外,门是新漆的桐油,门环却是旧铜,像被无数双手摩挲出来的包浆。门楣上悬一块乌木匾,“望舒小筑”字迹娟秀中透着风骨。这是江望舒亲笔题的,笔锋里隐隐还留着当年京中第一才女的气韵。让她觉得惊奇的是,门前竟无半点市侩烟火。没有蒸腾的白雾,只有一架小小的竹制茶棚,棚顶垂着半卷湘妃帘。帘内,一位着浅蓝罗衫的妇人正低头点茶。她背对他们,发髻松松挽起,只插一根紫檀簪,簪头垂下一粒珍珠,在日光里微微摇晃。洛曦宁心中猛地一颤,那并不是大伯母江望舒。这人是谁?心下疑惑刚起,却见到门外一人走了过来。洛曦宁定睛看去,那才是她的大伯母江望舒。没有她想象的落魄,没有暗淡的肤色,甚至没有一丝被烟熏火燎的痕迹。江望舒就只是站在门口,朝她笑望着。“宁宁?”声音不高,却带着笑。洛曦宁裙角扫过车前踏板,沾了些紫藤花瓣。她一步步走近,脚步踩在青砖上,竟生出几分迟疑来。“伯母……”不等她犹豫,江望舒已经来到了跟前,伸手握住她的手。她还未说话,一股茶香便扑面而来。“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提前来信?”江望舒笑着。洛曦宁张了张口,却只吐出一句:“我以为……”“以为什么?杜家娘子,我有客人,先上一壶茶吧!”江望舒莞尔,牵着她往院里走,“先进来喝盏茶,我再慢慢同你说。”院门“吱呀”一声,门内竟别有洞天。一条鹅卵石小径蜿蜒,两侧种着一些梅花,再往前是一方小小的水池,池水清澈,几尾红白相间的锦鲤悠然游着。池上架一座九曲竹桥,桥尽头是一间敞轩,轩窗全部支起,垂着淡青纱幔。纱幔上缀着细小的银铃,风过时,叮铃作响。倒是与那满墙的紫藤格外应和。那位杜家娘子快步走了过来,轩内下摆着一张紫檀茶案,案面嵌一块云石。案上是一套青瓷茶具,釉色如雨过天青。杜家娘子执一把银茶匙,正往小盏里舀茶粉。她的动作极慢,仿佛不是在点茶。“宁宁,尝尝,这是去年春末刚收的紫藤露。”点好的一盏茶,推至洛曦宁面前。茶色极浅,带着淡淡的紫,入口却是清洌的甜。洛曦宁抬眼,正对上江望舒的目光。江望舒笑笑,从旁边漆木食盒里拿出些茶点来摆好。“知道你喜欢吃甜的,这茶不喜欢就放着,吃些糕点吧。”“你以为我落魄,是不是?”江望舒轻声道,指尖抚过茶盏边缘,“其实,我比在蛮州城时更自在。”“我初来嘉州,确实只支了一口灶,卖茶粥度日。”江望舒的声音极轻,“后来,你伯父打了几场胜仗,商旅渐多。我便将茶粥铺子改成茶棚,又收了附近山里的野茶,自己来炒制。再后来,有茶商来找我合作,我便做了望舒的牌子。如今,嘉州镇六家茶铺,倒有四家卖的是我的茶。”“我虽然不如你会做生意,”她抬眼,眸中映着轩外摇曳的紫藤,“却知道怎样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茶要香,花要开,人也要自在。”洛曦宁环顾四周。窗棂半卷,风带着山泉的凉气穿堂而过,吹得纱幔上的银铃叮叮当当。,!旁边架子上,一排排茶罐贴着不同颜色的签条。她忽然想起当年蛮州城里的江望舒,那时的大伯父、堂兄并不在身边,她既要护住大姐姐,又要护住小儿子。日子过得着实辛苦,如今再看竟是比昔年在京中赏雪时,还添几分从容。洛曦宁端着茶盏,轻抿一口,“伯母你:()全家穿到流放前夕,手握空间赢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