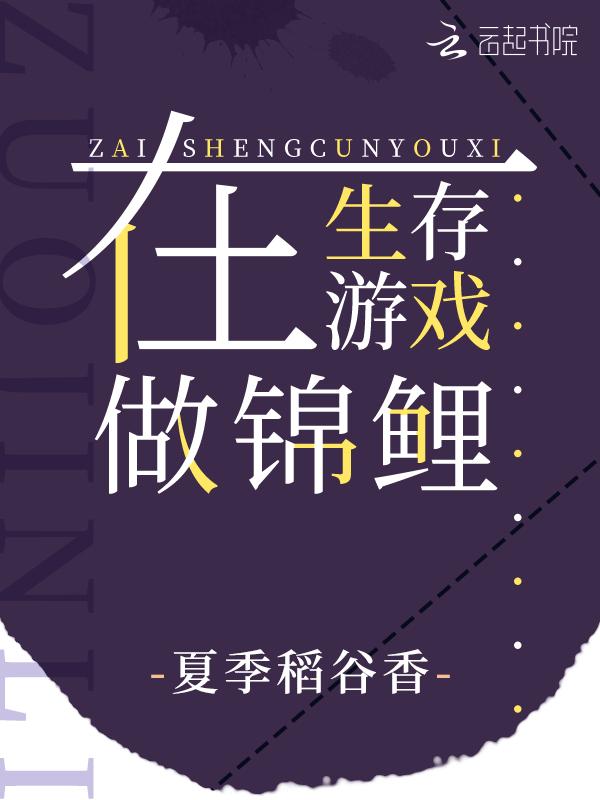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恋爱疗愈手册全文 > 第137章 恋爱是什么(第2页)
第137章 恋爱是什么(第2页)
开工第十五天,第一位访客来了。
是个藏族女孩,十六七岁,背着书包,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她是附近村小的学生,听说这里有座“不说话的房子”,特意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来看。她不会汉语,只用手比划着问能不能进去坐一会儿。
林小满带她进去,递给她一条毛毯。女孩蜷缩在角落的椅子上,盯着湖面看了整整三个小时,一动不动。临走前,她突然转身,紧紧抱住林小满,眼泪无声滑落。
那天晚上,林小满在日记本上写道:
>“她没说一句话,可我知道,她把整个童年都放在了那个拥抱里。”
越来越多的人闻讯而来。有人专程从北京辞职前来静居三天;有个抑郁症患者在这里住了整整一个月,每天只是看书、晒太阳、喂流浪猫;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带着儿子的骨灰盒走进来,在长椅上坐了一整天。离开时,她对着湖面轻轻说了句藏语,然后将一朵干花放在窗台上。
没有人追问她说了什么。
也没有人需要知道。
一个月后,纪念馆正式开放。没有剪彩,没有致辞,甚至连一块牌子都没有挂。只有湖边立着一块未经雕琢的石碑,上面刻着一行藏文和中文:
>“你可以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某天午后,林小满独自坐在馆内。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地板上,形成一片温暖的光斑。她脱了鞋,赤脚踩上去,温度恰到好处。陈默坐在对面画画,笔尖沙沙作响。小舟在门外修理漏水的水管,哼着一首老歌。
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林小满猛地抬头。
是阿?。
她瘦了许多,脸色苍白,但眼神清明。她手里提着一个旧录音笔,肩上背着行囊,像是走了很远的路。她看见林小满,嘴唇颤抖了一下,却没有立刻上前。
林小满站起身,一步步走过去。她们对视着,谁都没有说话。
最后,是阿?先哭了。
她打开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断续而温柔:
>“阿?,妈妈今天做了你喜欢吃的糯米糍。放在冰箱第二层……你回来记得吃。
>我知道你恨我赶你走。可我当时真的没办法……家里压力太大,亲戚都说你是怪物……
>但我从来没有后悔生下你。
>每次看到月亮,我都想你。
>如果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妈,我就搬到你身边去住。
>不管别人怎么说。”
录音结束,屋里一片寂静。
阿?哽咽着说:“她让我代她来看你。她说,谢谢你写了《沉默手册》。她终于敢说出这些话了。”
林小满抱住她,用力得几乎喘不过气。“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阿?抽泣着,“我不再害怕了。”
那天晚上,她们一起睡在帐篷里。阿?讲述这半年的经历:如何在缅甸边境教书,如何一字一句写下给母亲的信,如何在一个雨夜接到那通电话。“她说她梦见我回家了,穿着裙子,笑着叫她‘妈’。”
“然后呢?”林小满轻声问。
“然后她哭了,说对不起,说想我。”
林小满握住她的手:“那你原谅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