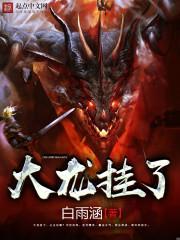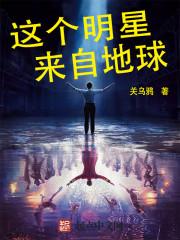奇书网>关我一个杂役什么事TXT > 第453章 你不比任何人卑贱我想和夫人浪迹天涯(第1页)
第453章 你不比任何人卑贱我想和夫人浪迹天涯(第1页)
零府后门。
求生欲极强的侍女还在不断地跟那两名侍卫求饶,祈求他们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自己一条生路。
事实证明她想多了。
他们并不想为了一个素不相干的侍女,而承担着有可能被慕容香兰发现的风险。
一旦被慕容香兰发现,他们擅自放了这名侍女。
那他们的下场,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
从零府后门出来,便是一条偏僻、隐蔽的胡同。
似乎是为了专门处理脏活而如此设计的。
“倒霉蛋,下辈子记得长点眼睛。”
两名侍卫将侍女丢到地。。。。。。
那一声铃响之后,天地仿佛重新呼吸。风动了,云移了,江河再度奔涌,鸟鸣重归林梢。可这世界已不同往昔??不是因为它骤然清明,而是因为人们终于明白:声音从不只属于喉咙,而真心也未必藏于言辞之间。
小葵走了,但她留下的回音,却在一代代人心中不断生长。那朵化石野葵被移入“言启纪念馆”中央,周围环绕着自她一生所绘《万声图》残卷中提取的声纹光带,日夜流转,如同未熄灭的灵魂之火。每年秋分,“回声祭”依旧举行,但不再有固定讲台,不再设定发言人。任何人,只要心中有一句非说不可的话,便可走上祭坛,用任何方式表达??哪怕只是静立片刻。
这一年,轮到一个名叫**阿稚**的女孩上台。
她七岁,先天失聪,从未听过这个世界的声音。她的父母是偏远山村的农人,识字不多,也不懂什么“赤心验语”或“未竟之塔”。他们只知道女儿喜欢画画,尤其爱画人脸,每一张都睁着大大的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听谁说话。
阿稚不会手语,也没接受过系统教育。她是靠着观察别人的表情、动作和唇形,一点点拼凑出这个世界的模样。她在沙地上画,在树皮上刻,在雨后的泥墙上用指尖勾勒线条。直到有一天,一位路过山村的“流动言塾”教师发现了她。
那天,教师正讲解“什么是真言”,问孩子们:“如果你有一句话能传遍天下,你会说什么?”
其他孩子争先恐后地喊:“我要当皇帝!”“我想飞!”“我希望妈妈永远不生病!”
只有阿稚蹲在一旁,默默掏出一块炭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天上落着雨,远处有火光。她把画递过去,眼神清澈而坚定。
教师愣住了。他认得这幅场景??那是三年前南方山火救援中的真实影像:一名女志愿者为保护孤儿,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滚落的火星,最终牺牲。当时全网刷屏,却没人记得她的名字。
“这是……你想说的?”教师轻声问。
阿稚点头,指了指自己的心,又指向画中女人的脸,然后做了个“听”的手势??手掌贴耳。
教师忽然红了眼眶:“你是想说,她虽然没留下名字,但你听见了她的心。”
阿稚笑了,用力点头。
那一刻,教师知道,这不是理解语言,而是直接触碰到了语言诞生之前的源头??**共感**。
于是他带着阿稚来到京城,在“非口语教育联盟”的协助下,让她接触情绪解码仪、脑波成像板、触觉共鸣阵列等工具。她仍不开口,但她开始用色彩、线条、震动频率来“说话”。她的作品被称为“无声告白系列”,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名为《母亲不说疼》,描绘的是一个女人深夜缝补孩子衣物时低垂的眼帘,窗外月光斜照,而她背上的影子却蜷缩如受伤的兽。
这幅画被录入“未竟之塔”第三层,成为首个以纯视觉形式收录的“真言”。
如今,阿稚站在“回声祭”的祭坛上,手中没有笔,没有仪器,只有一盒彩色粉笔。
她蹲下身,在石台上缓缓画了起来。
人群安静地看着。起初看不出什么,只见她一笔一划,细致得近乎虔诚。渐渐地,轮廓浮现??是一群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五官,唯独耳朵格外清晰,有的大如扇,有的蜷曲如芽,有的缠绕着藤蔓般的伤痕。
接着,她在圈子中央画了一颗心,裂开一道缝隙,从中飘出无数细线,连接到每一双耳朵。
最后,她在下方写下三个字,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
**听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