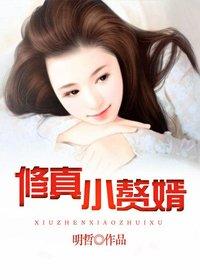奇书网>关我一个杂役什么事TXT > 第433章 杀人诛心看见二十八个亿还能忍得住(第3页)
第433章 杀人诛心看见二十八个亿还能忍得住(第3页)
每天清晨,总会有人排队等着进门。有农夫、书生、寡妇、逃犯……他们不说姓名,只讲心事。阿芜也不再只是听,有时会反问一句:“后来呢?”“你还记得她的眼神吗?”“你想让她知道吗?”
这些问题像种子,埋进人心深处。
某年冬天,大雪封山。
一个浑身结冰的小女孩被人抬上山来,唇色青紫,气息微弱。她是北境来的,父亲是当年那位士兵的战友,战死后被遗忘在边关。女孩一路跋涉,只为见阿芜一面。
“她说……”抬她来的老仆颤抖着,“她说只要见到你,就能听见爸爸最后的话。”
阿芜抱起小女孩,将她放在火炉边,轻轻握住她的手。
那一夜,她彻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小女孩睁开了眼,第一句话是:“爸爸说,对不起,没能带你去看海。”
阿芜哭了。
她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容器,也不是锚点,而是桥梁??连接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孤独与理解的桥。
又过了五年。
东岭书院不再是孤山一所学堂,而成了“说话之地”的中心。每年春日,都会有万人齐聚于此,举行“无名祭”??每人写下一件从未对人提起的秘密,投入火中焚烧。火焰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据说那是灵魂释放的光谱。
这一年,阿芜也写了一张纸条。
她把它折成一只小船,放进井中。
纸条上只有三个字:
**我怕了。**
船沉入水中,瞬间化作一道光流,顺着地脉奔涌而出。那一晚,全国数百个静语屋同时亮起绿光,许多人突然流泪,不知为何,只想抱住身边的人说:“对不起,我一直装得很坚强。”
而阿芜,在井边坐了一整夜。
直到黎明破晓,她才缓缓起身,走向菜园。
野葵花开得正好,光藤缠绕着篱笆,形成一道天然门户。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拉着她的衣角:“姐姐,我能在这里种一朵花吗?”
“当然。”她递给他一粒种子。
男孩认真地挖土、埋种、浇水,然后抬头问:“它会长大吗?”
阿芜蹲下身,与他平视:“只要你记得来看它,它就会一直活着。”
男孩点点头,蹦跳着离开。
阿芜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感到胸口一阵温热。
她解开衣襟,只见心口处浮现出一朵极小的光花,三瓣残缺,却不断旋转,散发出柔和光芒。那形状,竟与日记末尾画的野葵花一模一样。
她笑了。
原来真正的奇迹,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允许自己也被改变。
多年以后,当新一代的孩子们在课堂上学到这段历史时,老师总会问一个问题:
“神,到底存不存在?”
有的孩子说存在,有的说不存在。
但总会有那么一个孩子举起手,轻声说:
“我觉得,神是我们一起造出来的。当我们愿意听一个人说完他的故事,那一刻,我们就给了他一点点神性。而他,也把这份光还给了世界。”
教室窗外,正值春深。
一株野葵花悄然绽放,花瓣边缘泛起微光,像是在回应某种遥远的呼唤。
夏,又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