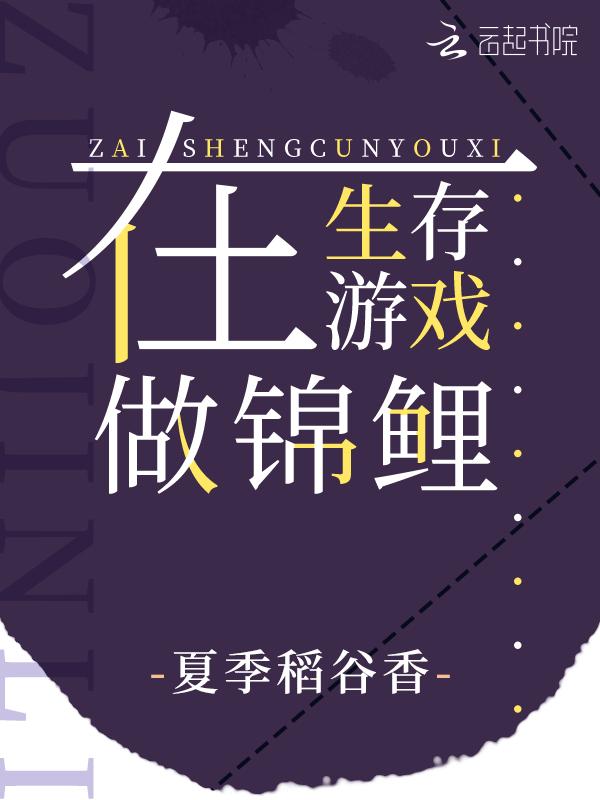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大唐怎么玩 > 第158章 没落的皇族血脉(第2页)
第158章 没落的皇族血脉(第2页)
李渊和孙思邈,都是一样的老人。
长孙皇后和萧皇后一样。
第二天早上,小公主去学堂前,还特地和长孙皇后说了一下。
长孙皇后点点头,送几个小丫头出了院子。
距离学堂不远,看著几个小丫头走远。
萧皇后和长孙皇后这才回到院子坐下,萧鈺给两人泡了一杯茶。
“这些茶比起之前茶有点,但也能凑合。”萧皇后笑了笑,“还是小郎君之前的好。”
长孙皇后端起茶杯嗅了嗅,“这个特挺好的,不错不错”
萧皇后笑了笑,目光转向院角孙思邈晒草药的木架。
那些草药摊得匀匀的,有的晒得半干,有的还带著潮气,显然是按药性分了时辰晒的。
“我这阵子住下来,看孙先生做事,感触良多。”
“先生晒草药,从不等著正午的大太阳猛晒,总说『草药有性子,燥性的得阴乾些,湿性的得晒透些,急不得。”
“前几日有村民来问诊,咳嗽得利害,孙先生也没开猛药,只让他每天清晨去潭边吸些凉气,喝些煮透的梨水,说『肺气得顺,硬压反而伤了根本。”
萧皇后顿了顿,转头看向长孙皇后,眼神里满是过来人的温和:
“你这身子,跟那些需要细养的草药、需要顺气的病人一样,最忌『急和『忧。”
“宫里的事,二郎是个有主张的,你不用事事都掛在心上。”
“孩子们在这儿,有学堂、有伙伴,比在宫里自在,也不用你天天盯著。”
“我刚住来时,也总想著长安的旧事,后来看孙先生,每天就晨练半个时辰,晒药、喝茶、跟老爷子聊聊天,日子过得慢,可身上的劲儿倒比在宫里时足。”
“他常说『心不扰,身自安,这话是真的。”
“之前我总觉得,做长辈的就得把所有事都扛起来,才算尽了责。”
萧皇后轻轻嘆了口气,语气里多了几分释然:
“可在这儿住久了才明白,有些事啊,顺其自然比强撑著好。”
“就像孙先生调理身体,从不说『这病得立刻好,只说『顺时吃饭,顺气安神,日子久了,反而比吃多少补药都管用。”
“你啊,也別总跟自己的身子较劲,宫里的事能放就放放,孩子们的事让她们自己闯闯。”
“每天跟著我晒晒太阳、喝喝茶,听听孙先生说些草药的道理,心先静下来,身子才能慢慢养过来。”
长孙皇后看著萧皇后温和的眼神,又望向院角孙思邈慢悠悠翻晒草药的身影,指尖的凉意似乎散了些。
她轻轻喝了口茶,薄荷的清香在嘴里散开,低声道:“婶婶说的这些,我竟从未细细想过。”
“总觉得操心是该的,却忘了自己的身子才是根本。”
“往后,我听婶婶的,试著少些掛心,多学学孙先生这份『慢。”
萧皇后笑著拍了拍她的手:“这就对了,你看这院子里的日子,不慌不忙的,反而事事都顺。”
“宫里的事、孩子们的事,也都有它们的理,急不来,顺其自然,反而能落个心安。”
院角的薄荷香混著老槐树的清苦,慢悠悠绕到鼻尖。
长孙皇后捧著温热的茶碗,指尖终於不再像在宫里那样泛著凉。
她望著方才小丫头们跑远的方向,石板路上还留著她们踩过的浅痕,心里忽然空落落的。
却不是宫里那种被琐事填满的慌,是种鬆快的、带著暖意的空。
在宫里时,天不亮就要起身处理后宫诸事,各宫的用度,连尚食局的菜单都要细细过目。
那时总觉得“操心”是本分,是皇后该扛的责任,可心里的弦却总绷著,连喝口茶都要想著“这茶是否合各宫的口味”。
可在这里不一样。
早上不用被宫人的请安声叫醒,能听著潭边的鸟鸣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