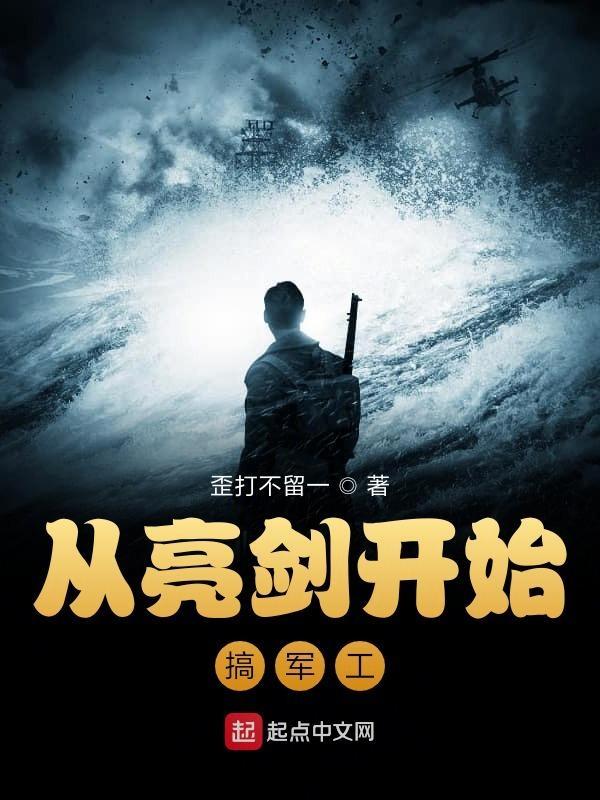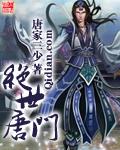奇书网>塌房我拆了你这破娱乐圈免费阅 > 第516章 jove brain发起挑战无人敢应(第3页)
第516章 jove brain发起挑战无人敢应(第3页)
“各位,”他说,“请闭上眼睛三十秒。”
全场安静。
他按下播放键。
起初是空白,接着,一段稚嫩的女声响起,带着电流杂音和发音不清的“mama”;然后是风穿过葡萄架的沙沙声;再后来,是金属撞击的节奏、咳嗽后的喘息、一句用合成器拼出的“我想回家”……
三十秒结束。
他睁开眼,看见许多人脸上挂着泪。
“刚才你们听到的,”他说,“是一个听不见世界的孩子努力发声的过程,是一片沙漠清晨的生命律动,是一个濒死少年最后的心跳回响。它们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美’,可它们真实存在。而我们的文明是否进步,不在于它能生产多少完美作品,而在于它能否容纳这些不完美的声音,并赋予它们同等的尊严。”
掌声雷动。
三天后,消息传来:《众声》入选格莱美“最佳新世纪专辑”初选名单。
国内舆论再度沸腾。有媒体称其“为中国音乐赢得世界尊重”,也有嘲讽称“不过是靠卖惨拿奖”。
周南对此一笑置之。他在社交平台写道:“奖项从来不是终点。真正的荣誉,是那个曾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的孩子,今天主动拿起录音笔,对自己说:‘我在。’”
春天深了。
“声音种子计划”迎来新一轮扩张,新增三十所学校,重点覆盖西南山区与边疆团场。团队开发出低成本便携录音包,内含防水麦克风、太阳能充电板与简易混音APP,可通过卫星网络上传作品。
阿依古丽寄来一封信,附着一张照片:她戴着新送的设备,站在学校屋顶,身后是连绵雪山。信上说:“我现在能录下整条河的声音了!我想做一首关于冰川融化的歌,提醒大家保护水源。”
肖萌回信时附上一段音频:女儿爬行时膝盖摩擦地毯的声响,配上她咿呀学语的呢喃。“送给你当灵感。”她写道,“有些声音很小,但它们都在讲述生命的坚持。”
某个雨夜,父女俩在客厅玩“声音猜谜”游戏。周南模仿猫叫、汽车鸣笛、开水壶沸腾,女儿咯咯笑着一一辨认。最后一轮,她突然凑近父亲耳朵,用力吹了一口气。
周南装作没听见:“这是什么声音?”
她急了,伸手拍他肩膀,大声喊:“呼??!是我呀!”
那一瞬,空气凝固。
他猛地转头,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她咧嘴笑着,又喊了一遍:“我??呀??!”
雨水敲打着窗户,城市的灯火在湿漉漉的玻璃上晕成一片光海。
他一把将她抱起来,转了整整一圈,笑得像个少年。
肖萌从厨房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汤勺,眼里全是泪。
他们没有说话,只是紧紧相拥,任凭那个笨拙却无比清晰的声音,在房间里一遍遍回荡。
这世上总有太多声音被淹没:哭泣被当作软弱,沉默被解读为顺从,挣扎被视为失败。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愿意开口,还有一双手愿意记录,还有一颗心不肯熄灭??
光,就永远不会彻底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