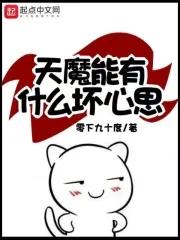奇书网>恋爱疗愈手册笔趣阁txt > 第132章 绝望小女仆(第3页)
第132章 绝望小女仆(第3页)
小舟沉默片刻,抬头看她:“那你告诉我,当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是谁陪你熬过去的?”
林小满愣住。
“是你自己录下的那句‘我还在这里’。”小舟轻声说,“不是某个程序,不是某个虚拟形象,是你自己的声音,提醒你自己你还活着。”
她心头一震。
那一夜,她再次开启录音笔:
“今天我们谈‘效率’,谈‘智能化’,却忘了最原始的情感交换才是疗愈的核心。机器可以记录,但无法共鸣;它可以回应,但无法等待。而真正的倾听,常常发生在沉默里,在对方还没准备好说出口的时候,在眼泪落下之前的那一秒停顿中。”
“我们不怕科技进步,怕的是人心退场。”
“那位程序员朋友,谢谢你让我看到这个问题。我想告诉所有正在研发情感AI的人:请不要取代倾听,而是帮助更多人学会彼此倾听。”
“真正的疗愈,从来不是‘有人替你承担痛苦’,而是‘有人愿意陪你一起经历它’。”
录音结束,她走出屋子,仰望星空。
远处,一只萤火虫缓缓飞来,落在风信子的叶片上,微光闪烁,如同一句未说完的话。
她忽然想起京都那位老教师,想起他放入溪流的玻璃瓶,想起他说的那句“现在轮到我来说了”。
她转身回屋,打开地图软件,搜索“云南大理五月十二日邮政编码”。
几分钟后,她订下了一张前往大理的车票,出发日期:三天后。
临睡前,她给苏晓留了条语音:“我要去一趟大理。可能找到周晚最后的足迹。《听见》第57章,我想亲自完成它。”
第二天清晨,她整理行装时,发现桌上多了一封信。
没有署名,信封上画着一朵简笔风信子。
她拆开,里面是一张手工卡片,字迹稚嫩却认真:
>林姐姐:
>
>我是昨天那个想录音却不敢开口的初中生。回家后,我对着手机说了十分钟话。我说我很害怕考试,怕爸妈失望,怕同学笑话我戴助听器。我说完之后,把录音删了。
>
>但我记得我说过。
>
>今天我去学校,主动举手回答了一个问题。老师说我声音很小,但全班都安静下来听了。
>
>原来,只要我说出来,世界真的会停下来听。
>
>下次,我会录一段完整的语音给你。
>
>??一个正在学习说话的孩子
林小满将卡片夹进周晚的手稿里,嘴角扬起温柔的弧度。
中午,李远来了。
他带来一份文件:《“回声计划”伦理准则(草案)》,其中明确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