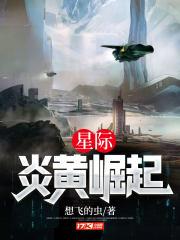奇书网>让文物活起来的策划方案 > 第十七章 政务厅里跑执照漕瀆边共守摊位(第1页)
第十七章 政务厅里跑执照漕瀆边共守摊位(第1页)
第二天上午的阳光,刚把小西街漕瀆边的青石板晒得微暖,林砚就看见那辆熟悉的黑色警车停在巷口。
周明从驾驶座下来,黑色衝锋衣的拉链拉到胸口,露出里面的藏青警服领口,手里拎著个文件袋,脚步比平时慢了些——昨天她值夜班,眼下还带著点淡青色,却没影响眼神里的利落,远远就朝林砚挥手:“走,先去区文旅局,就说你是我调研的非遗项目传承人。”
林砚赶紧把刚整理好的文创样品放进布包,里面还裹著那枚被雨水淋过、重新绣好金线的渔翁胸针——苏桂兰凌晨四点就起来拆旧线,手指被针扎破了两处,贴了创可贴还在渗血。“麻烦你了周队,还让你特意跑一趟。”林砚跟上她的脚步,闻到她衝锋衣上淡淡的消毒水味,混著市河的水汽,是常年出警留下的味道。
区文旅局在老办公楼的三楼,走廊里舖著褪色的红地毯,墙上掛著“湖州非遗保护成果”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小西街的钮氏状元厅。
周明熟门熟路地敲开“非遗科”的门,里面的科员老杨正对著电脑填表格,见他们进来,赶紧起身:“周警官,你说的调研对象就是这位?”
“杨科,这是林砚,做苏氏非遗文创的,手里有光绪年的染谱和老绣技。”周明把文件袋里的染谱复印件、文创样品推过去,语气自然得像真在做调研,“他现在想把文创推广出去,但资金和合规手续都卡著,你看能不能走『小微企业非遗补贴的通道?”
老杨拿起染谱,指尖蹭过复印件上的“靛蓝配色”字样,又捏起胸针对著光看:“这针法是『水色针吧?湖州没几个年轻人会了。”他翻出补贴申请表格,递给林砚:“你填下基本信息,把文创的成本、用途写清楚,我帮你走加急流程——最近区里正好缺非遗活化的案例,你的项目符合要求,应该能批。”
林砚握著笔的手有点发紧,表格上的“申请金额”栏,他犹豫著要不要填1万,周明却在旁边轻声说:“填1。5万,够你买丝线和包装材料,还能剩点备用。”林砚抬头看她,周明冲他眨了下眼,眼神里藏著“放心”的意思。
填完表,老杨拍了拍桌子:“三天內给你消息,批下来直接打你银行卡里。对了,摆摊的执照,你让周警官带你去政务大厅办『临时性文化经营许可,提我名字,能简化流程。”
从文旅局出来,周明直接开车去政务大厅。
下午的大厅人不多,周明熟门熟路地找到“综合窗口”,跟工作人员说了几句,递上林砚的身份证和文创项目说明。“之前衣裳街举报你的事,我跟管委会沟通过,以后你在小西街、状元街摆摊,只要有这个许可,没人能隨便赶你。”周明帮林砚整理材料时,林砚看见她右手食指第二关节的厚茧,蹭过表格边缘的毛边,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痕跡。
许可办得很顺利,红色的印章盖在纸上时,林砚心里突然踏实了——之前怕被举报、怕不合规的焦虑,好像都被这枚印章压下去了。
他把许可小心地折好,夹在《苏氏染谱》的扉页里,染谱上太奶奶的字跡,和许可上的公章叠在一起,像是新老传承的呼应。
“晚上有事吗?”周明突然问,“我下班没別的事,去你摊位帮忙卖东西吧,正好看看文创的实际反响。”
林砚愣了一下,赶紧点头:“当然好,就是……要麻烦你了。”
傍晚的小西街亮起了灯笼,漕瀆边的摊位渐渐热闹起来。
林砚的摊位摆在西岸美术馆隔壁,蓝布上的金线渔翁胸针,在灯笼光下泛著温润的光。
苏桂兰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著丝线补绣坏的书籤,夏晓雨正对著手机跟汉服博主连麦,介绍文创的来歷。
周明是穿著衝锋衣来的,刚下班没换衣服,袖口还沾著点出警时的泥土。“我来喊吧。”她拿起一枚胸针,走到漕瀆边的河埠头,声音清亮却不张扬:“路过的朋友可以看看,苏氏非遗文创,手工苏绣胸针,用的是光绪年的染谱配色,每枚都要绣两小时。”
有个带孩子的妈妈凑过来,孩子指著胸针上的渔翁:“妈妈,这个爷爷在钓鱼!”
周明蹲下来,跟孩子平视:“这是湖州的老手艺,叫苏绣,你看这渔翁的蓑衣,是用特別细的金线绣的,要一针一针慢慢绣,就像搭积木一样,得有耐心才能做好。”孩子听得入神,妈妈笑著买了一枚,还加了林砚的微信,说“以后出新品要通知我”。
林砚站在摊位后,看著周明跟顾客交流,突然发现她的衝锋衣袖口——左边袖口磨破了,灰色的內衬露出来,毛边被风吹得轻轻晃,像是已经磨了很久,却没来得及补。
他想起周明平时总穿这件衝锋衣,出警、查案、帮他跑手续,从来没见她换过別的外套,心里突然有点发暖,悄悄掏出手机,点开购物软体,搜“黑色衝锋衣”,把周明衝锋衣的款式记在心里。
“小林,帮我拿个书籤!”周明回头喊,手里举著两张百元钞,“这位先生要一套胸针加书籤,还说要多买两个送朋友。”
林砚赶紧递过书籤,看著周明熟练地打包——她把文创放进青黛色的包装纸里,还学著苏桂兰的样子,用金线系了个小蝴蝶结,动作虽然有点生涩,却很认真。
“周队,你怎么还会打包啊?”夏晓雨凑过来,语气惊讶。
周明笑了笑,指尖蹭过包装纸上的染谱纹样:“之前查文物走私案,跟博物馆的老师学过包装文物,差不多一个道理,都要仔细点。”她顿了顿,又拿起一枚胸针,“你们这文创做得好,有老手艺的魂,比泽家那些仿品强多了。”
苏桂兰也笑著说:“周警官要是不忙,以后常来,我教你绣简单的图案,不难。”
周明点头:“好啊,等这个案子结了,我就来学。”
夜色渐深,漕瀆上的灯笼倒映在水里,像一串流动的星星。
周明帮著收摊时,主动把重的摺叠桌扛起来,衝锋衣的下摆扫过青石板,磨破的袖口偶尔蹭到林砚的胳膊,带著点粗糙的质感。
“今天卖了12个胸针、8个书籤,赚了1384块!”夏晓雨数著钱,语气兴奋,“比昨天在衣裳街好多了,多亏了周队帮忙!”
周明把桌子放进小推车,擦了擦额头的汗:“主要是你们的文创好,我就是搭把手。补贴的事我会盯著,批下来第一时间告诉你。”
林砚推著小推车,送周明到巷口的警车旁。周明拉开车门时,林砚突然说:“周队,你……你衝锋衣的袖口,要不要我帮你补补?我会点针线活,之前修復古籍时学过。”
周明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磨破的袖口,笑了:“不用麻烦,我自己缝缝就行。你赶紧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警车发动时,林砚站在巷口,看著车尾灯消失在小西街的尽头。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购物车里还存著那件黑色衝锋衣,尺寸是他悄悄根据周明的身高估的——他想等下次补贴到了,就买下来送给她,不用她说谢谢,只要她不用再穿磨破袖口的衝锋衣就行。
漕瀆边的灯笼还亮著,风吹过染谱的纸页,发出轻微的响声,像是太奶奶在轻声说“谢谢”。林砚知道,有周明这样的朋友帮忙,有苏桂兰和夏晓雨一起努力,他们的文创,一定能在湖州的老街上,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