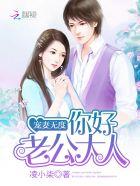奇书网>局里来了年轻人 电视剧 > 第8章(第2页)
第8章(第2页)
“警察!开门!例行检查!”
穿着制服的民警用力敲打着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声音在狭窄的楼道里回荡。
门内传来一阵慌乱的碰撞声和压抑的惊叫。
半晌,门才被一个眼神涣散、骨瘦如柴的年轻人打开,一股混合着汗臭和某种化学制剂酸败气味的热浪扑面而来。
屋内一片狼藉,桌上还散落着几片残留着诡异蓝色的锡纸和吸管。
“又是‘这玩意儿’。”带队的老民警眉头紧锁,示意同事将瘫软在地、显然刚吸食过的年轻人控制住,进行现场取证。
这已经是本周在同一片区发现的第三起涉“蓝冰”案件了。
然而,就在这栋楼的顶层,另一间房门紧闭的出租屋内,气氛却截然不同。
昏暗的灯光下,交易正在进行。
卖家是个油头粉面的青年,他神秘兮兮地从包里掏出一个更小巧、包装更花哨的塑料袋,里面是几颗晶莹剔透、泛着诱人光泽的“糖果”。
“兄弟,‘蓝冰’过时了,劲儿小还容易被抓。试试这个,最新款,口感好,上头快,关键是……现在市面上还没几家有,新鲜!”他压低声音,带着一种推销自家产品般的得意。
男子将信将疑地捏起一颗,对着光看了看,那粉红的色泽确实更具迷幻性,“真这么神?”
“骗你是孙子!听说上头换了更厉害的料,保证你试过一次就忘不了!”卖家拍着胸脯保证。
楼下,是“蓝冰”吸食者被戴上手铐的麻木面孔,和民警疲惫却坚定的身影。
楼上,是“它”带着甜美伪装悄然流入市场的第一波暗流。查禁与迭代,抓捕与顶风,在这栋破旧的居民楼里,形成了不同的画卷。
正如一位老禁毒警常说的:“我们拼尽全力在扑灭上一场火,而新的火种,往往已经在灰烬下悄然复燃。”
午后烦躁、静默,大家都蔫了吧唧的。
廖繁春毫无形象地趴在桌面,手里的文件扇得呼呼作响,嘴里嘟囔着:“啥天儿啊,忒熬人了这也,还没过季呢!我感觉自个儿已经像那蒸笼里的叉烧包,就差葱花了。”
这地道的“抱怨”,在一片略显沉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兀,却也带来了一丝活气。引得几个本地同事忍不住偷笑,连一向严肃的林诚武都几不可查地弯了弯嘴角。
张锦坐在她对角线的工位,指尖正在键盘上飞舞,追踪一条模糊的资金流水线索。
听到廖繁春的话,她推了推滑落鼻梁的眼镜,目光扫过那人因为闷热而微红的脸颊,还有额角被汗水濡湿的碎发,视线最终落在她不停扇风的、骨节分明的手上。
两年前初遇时,就是这双手,利落地制服了人贩子,袖口沾着碎发,带着一股陌生的、蓬勃的生命力,撞进了她按部就班的世界。
“心静自然凉。”张锦垂下眼,声音依旧是平和的,听不出波澜,“或者,你去把证物室那几箱旧档案整理一下,那里阴凉。”
廖繁春立刻坐直了身子,垮着脸:“别啊,张老师!那地方进去都能拍《聊斋》了,我这阳气…不足,顶不住。”她夸张地抱了抱胳膊,成功引来更多低笑声。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姜琏琏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没了往日的活泼,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兴奋和凝重的神色。
她手里拿着一个密封的证据袋,里面是几颗看起来如同普通冰糖,却隐隐泛着不正常的淡粉色结晶。
“锦姐!廖姐!还有呃……林队?”姜琏琏的声音有点急,瞥见林诚武这个熟透了的“新成员”还是有些不适应,又马上恢复了神情,“技术处刚出来的结果,城南酒吧街新流进来的货,不是‘蓝冰’了!”
一句话,让办公室里所有的闲聊和懈怠瞬间消失。
张锦立刻起身,接过证据袋,走到光线更好的窗边仔细观察。廖繁春也收敛了玩笑神色,凑了过去,眉头微蹙:“这啥玩意儿?长得跟水果糖似的。”
“我们暂时叫它‘红色玛丽’。”姜琏琏语速很快,“外观更具迷惑性,初步检测,成瘾性比‘蓝冰’至少高出三成,而且……代谢更快,更难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