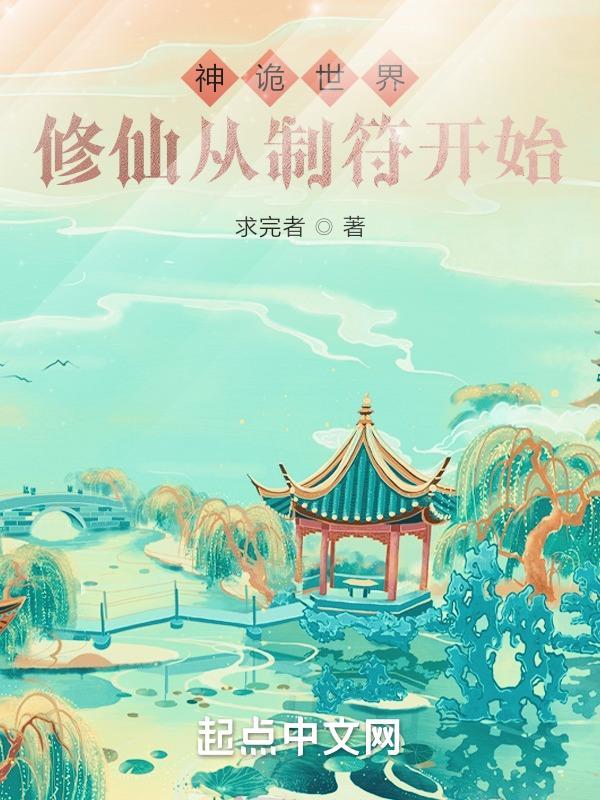奇书网>我的饭馆通北宋全文免费阅读 > 277 师徒携手入宫(第1页)
277 师徒携手入宫(第1页)
官家遣人出宫采买坊间市食,并不稀奇,临近大内东华门的食肆,但凡稍具规模,门外无不挂有“御前”二字,皆曾向宫里进献过菜肴。
但入宫设摊……何双双入行多年,从未听闻哪家食肆曾得此殊遇。
见三人。。。
十月十日,天未亮透,吴铭便已起身。窗外秋风微凉,檐下铁马叮当,院中桂树洒落一地碎金。他站在灶前,将昨夜腌制的牛腱子取出,肉质紧实,色泽红润,浸在秘制卤汁里已有十二个时辰。这是为今日宫中设摊特备的头道菜??五香酱牛肉。
张供奉早在昨日就打过招呼:“莫要拘束,照常做便是。”可哪能真个照常?这“常”字背后压着的是大宋天子的胃口、龙庭百官的目光,乃至整个汴京城食客的耳朵。吴铭心里清楚,这一回出摊,卖的不是钱,是名声;吃的不是饭,是命途。
卯时三刻,餐车推入后巷。那辆巧匠打造的新式餐车通体乌木包铜角,四轮嵌滚珠轴承,推起来无声无滑,顶上支起一方素绢幡旗,墨书“吴记夜市”四字,笔力遒劲,乃是前些日子一位醉酒老学士题赠。此刻幡旗未展,因按礼制,入宫不得张扬字号,须待圣谕准许方可挂出。
李宪亲自带人来接,八名内侍抬着冰鉴、炭炉、锅碗瓢盆随行,另有两名尚食局小吏捧册记录菜品来源与火候流程。吴铭看得皱眉??这不是来吃,是来查账的。
“莫紧张。”李宪低声笑道,“尚食局不过是走个过场,今上说了,若你做的菜合口,往后每月初十都可入宫一次,设个小摊,权当消遣。你只管放手去做,其余事自有我担着。”
吴铭点头,心中却不敢松半分。他知道,赵官家虽仁厚,可宫闱之内,一步错便是万劫不复。一道菜咸了淡了或许无妨,但若让御膳房那些老油条抓到把柄,说他“以市井粗食僭越龙膳”,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
巳时初,宫门开启一道窄缝,禁军查验腰牌后放行。一行人穿永巷、过拱宸门,绕保宁殿侧廊而行,沿途朱墙巍巍,琉璃瓦映日生辉。忽闻钟声三响,远处垂拱殿方向有仪仗列队而出,黄伞飘摇,玉磬轻鸣。
“是官家移驾琼林苑!”李宪低声道,“快些,已在等了。”
琼林苑本为科举放榜后赐宴之所,此时秋景正盛,枫叶如焰,菊丛似雪。临水亭台已被清空,中央摆开一张紫檀长案,两侧设绣墩十六,显然是为近臣陪宴所备。案上无陈设,唯有一副银筷、一只青瓷碗静静搁着,竟无其他器皿。
吴铭心头一跳:这是要现场烹制?
李宪会意,忙上前禀报:“启禀圣上,吴掌柜已至。”
亭内传来一声温和的“宣”。
吴铭整衣入内,抬头只见一人端坐主位,身着赭黄袍衫,头戴折上巾,面庞清癯,眼神温润却不容逼视。正是当今官家赵顼。
“免礼。”赵顼抬手,“听李中使言,你那卤味极尽风味之妙,朕心向往久矣。今日特召你入苑,不拘礼数,便如街边一般施为即可。”
吴铭叉手拜下:“臣遵旨。”
话音落,他转身走向餐车,揭开木盖,一股浓香顿时弥漫开来。先取砂锅一只,倒入老卤,置于炭炉之上煨热;再将牛腱子切片,码入盘中,配以酸?头、嫩姜丝、香菜末三样小料。又另起一锅,煮鸡蛋六枚,剥壳后浸入卤汤提味。
围观诸人皆屏息凝神。一名年轻官员忍不住凑近嗅了嗅,叹道:“此香非人间所有,直似从《东京梦华录》里走出来的。”
吴铭不理,专注手中活计。接着取出自制辣椒油,暗红透亮,浮着芝麻与花椒碎,这是蜀地技法融合汴京口味的独门秘方。轻轻淋上一圈,香气陡然升华,辛辣中带着醇厚回甘。
“好!”赵顼抚掌而笑,“光看这一手泼油,便知火候拿捏得极准。寻常厨子怕辣气冲鼻,总不敢烫得太热,唯有真正懂行者,才知七成热油方能激出椒麻魂魄。”
吴铭躬身道:“官家明察秋毫。”
此时卤汤沸腾,吴铭执长筷夹起一片牛肉,在空中略停片刻,让多余汤汁滴落,而后稳稳放入青瓷碗中。动作行云流水,毫无滞涩。
“请圣上品鉴。”
赵顼亲执银筷,夹起牛肉送入口中。咀嚼片刻,双目微闭,似在细细体味。良久,方才睁开眼,露出笑意:“筋而不柴,酥而不烂,咸鲜之中藏甜,麻辣之后回甘……妙啊!难怪百姓趋之若鹜。朕尝遍御膳珍馐,竟未有如此接地气却又登峰造极之味。”
身旁一名老臣试探问道:“敢问吴掌柜,此卤可用了多少药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