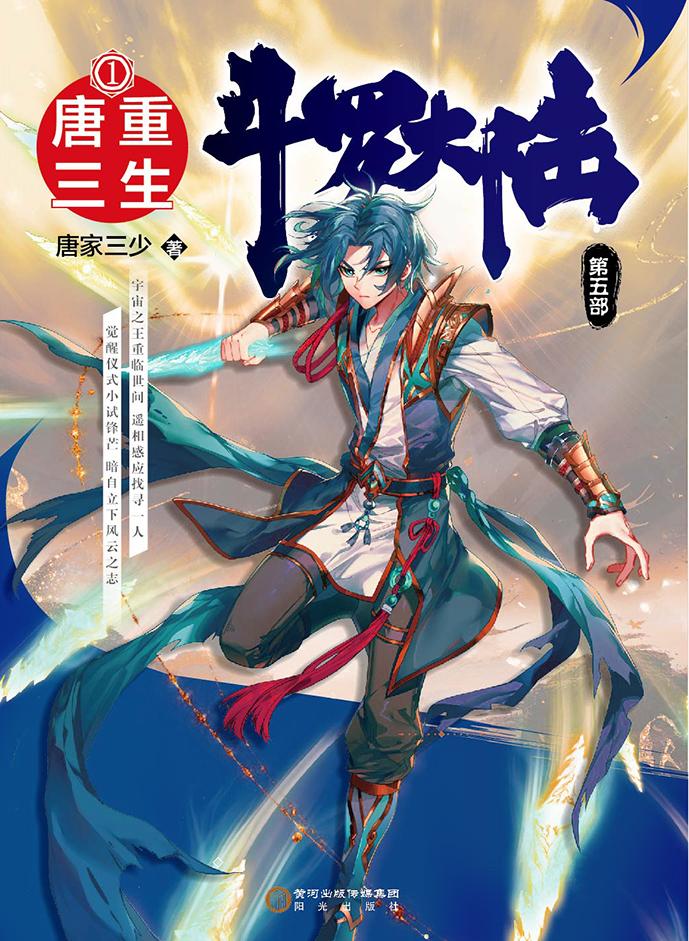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曾静一梦千年 > 光影(第1页)
光影(第1页)
贞观九年冬,含风殿中,帷帐低垂,檀香袅袅。春日的阳光从雕花窗棂中斜斜落下,照在病榻上。
李渊面色苍白,气息微弱,目光却依旧炯炯有神。他望着榻前的李世民,声音沙哑:“二郎……我这一生,纵有得失,却终究把这天下打了下来。如今大唐安稳,你也做得很好。”
李世民双膝跪地,紧紧攥住父亲的手,泪水在眼眶打转。他心中翻涌着无数往事:晋阳起兵时父子并肩的豪情、长安城头迎风猎猎的旗帜、玄武门的弓箭与鲜血,让他至今仍有愧意。
“父皇……”他的声音哽咽,“儿臣有不孝之罪,至今难安。但儿臣愿竭尽余生,让大唐永固,让百姓安宁,不负父皇所开基业。”
李渊目光微动,似有痛意,却又渐渐释然。他缓缓抬手,指向殿外:“听……鼓声远,马蹄声轻。那是天下太平的声音。二郎,你比为父更懂这江山……朕,放心了。”
话音渐弱,手也无力垂下。
殿中一瞬寂静,唯有风吹过帘幔。
李世民死死跪在榻前,久久未语,泪水悄然落下,滴在父亲衣袖上。长孙皇后缓步上前,轻轻扶住他肩头,低声道:“陛下,节哀。高祖皇帝的基业,如今在你手中,必会万世不朽。”
殿外,文武百官已齐集,闻报太上皇薨逝,皆俯身痛哭。贞观九年的悲痛慢慢远去,而作为穿越者,我明白真正的悲痛才刚刚开始。
贞观十年初,我听闻皇后开始频发气疾,思即此事,我悲痛难安,我常在夜深人静时,燃起檀香,虔心抄写佛经,为皇后祈福。
笔尖摩挲纸面,每一字都承载着我深深的祝愿:“愿这病痛更轻些。”同时也是我的愧疚:“也许我的到来或多或少打扰了她和李世民之间的感情。”也有我的感激:“自来长安以来,皇后待我很好,送风宴那次更是亲自为我解围。”
我时常自请入宫。虽然立政殿常有侍从、宫人陪伴,皇后娘娘仍能看出我心意真诚——或是我虔诚诵经后沾染的气息,或是手上未散的墨香,使她微微一笑。
于是,我与皇后的关系日渐亲近。日常间,我会为她讲些趣闻轶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或是西域突厥的奇闻异事。她听得入神,偶尔轻笑,让我心头涌起一丝温暖。
李世民亦对我极为信任。平日政务繁忙,他放心我时常陪伴皇后,知我不会越制,只为安抚皇后、维持宫中和顺。那段日子,虽心有悲痛,却也因皇后的微笑与李世民的信任,生出一份淡淡的慰藉。
那日,我侍坐于立政殿,案上摊着数卷未批的文书。皇后手执朱笔,写了两行,忽觉头晕,缓缓放下笔。
她抬眼看我,目光温和却带几分探究:“这些事,你看该如何处置?”
我心中一震。那一刻,我明白,她已开始试着让我替她分担宫中事务——六尚奏请、织造更替、宫膳份额,皆是旧日唯她亲批之事。
“娘娘……”我俯身欲辞,她却轻轻一笑,声音微弱:“陛下信你,本宫也信你。你心思细,知分寸,若有一日我病重不能理事,你替我看着些,也好。”
她说得极轻,仿佛只是随口一叹,可那几句话却如重石压在我心口。
我暗自心惊。
我知道,这世上唯有皇后能与李世民并肩而坐,她的地位无人可替。可她此刻的眼神,却仿佛在将那一份“托付”也一并交给我。
我垂下眼,定了定神,温声答:“娘娘多虑了。臣不过偶尔侍侧,岂敢妄涉宫务?陛下与娘娘情深,天地可鉴,臣若妄有非分之念,必为天地不容。”
皇后静静看着我,许久,眼底掠过一抹淡淡笑意。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知你不会。”她轻声道,“正因如此,我才放心。”
窗外春风微起,吹动殿内的帘纱。
我跪在她榻前,望着那一袭素衣,心头一片酸楚。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
她并非真想让我替她,而是隐隐察觉,若她不在,我或许会成为李世民心中最特别的那个人。
她在试探,也在安放。
而我,唯有以退为敬,以心相护。
不久后,皇后病势更重,卧于榻上已难久坐。立政殿的政务仍日日送至殿中,我便奉她之命,在旁一一整理,依章拟答,再呈她审阅。
那一日午后,阳光微暖,照在金漆的几案上。皇后靠在锦枕间,神情恬淡,指尖轻摩着念珠,声音微弱:“陛下政务繁重,后宫诸事若不及时奏报,反添烦扰。你暂代我批过,等我病稍缓,再一并呈请。”
我执笔低首,轻声应“诺”。
笔尖在纸上划过,字迹一行行铺开。那一刻,满殿的静默仿佛都凝在笔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