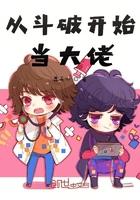奇书网>死敌总想和我官宣[娱乐圈 > 第 2 章(第1页)
第 2 章(第1页)
尚随清罕见的慌了神,告辞元疆饶匆匆下车,就看见学堂大门禁闭,只有管仪一人站在门口清点满地货物。
元疆饶的马车渐渐走远。
管仪好奇的目光看了一眼,她在京中做生意,自然有几分眼力,看出这马车主人身份非凡,还没发问就被尚随清摇着胳膊唤回注意力。
“怎么了?”尚随清问。
“宫中来了人,他们便都闻了味缠上来。”管仪下巴一扬,尚随清看向那被挂起的金字招牌。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同文学堂”。
管仪三两句解释清缘由,她写好单子又安顿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把东西送回去。
正是尾声,她撂下手头的事愤愤不平道:“你落难时我一个个求上门,都置若罔闻,现在倒是消息灵通。”
尚随清知道管仪处理起这种事来得心应手也不在多说,只是宽慰她不必生气。
“谁送你回来的?”管仪问。
她握着尚随清的手刚想捂捂,却发现她双手出乎意料的暖。
“关彧元家的人。”
管仪露出忧色,世家子弟多骄纵。
尚随清想起更要紧的事:“阿姐,先不说这个,这个冬天我恐怕会越来越冷。”
她其实拿不准这推断的准确率有多高,但棉碳价格高居不下、况且刚刚初冬便下起了大雪,种种异象让她不得不担心。
可要如何做又是个大难题。
尚随清捂住脑壳,痛痛地拉着管仪进了学堂中。
她拿出下狱前做好的物件,几日未曾下雨落雪,黑色蜂窝状的煤炭已经干燥。
尚随清将东西放入炉中点燃,大开门窗,手上功夫不停,把积压几日的学堂事务处理起来,静静等着记录蜂窝煤的燃烧时间。
材料易得,制作简单,关键在于模具和推广,有了这件东西,这个冬天无论是学堂还是百姓,日子都不会难过。
碳火从日头正盛烧到日落西山。
当街熙攘,寒风瑟瑟,尚随清高高抬起手比划了个数字。
“两文钱的碳,便可持续燃烧近三个时辰。”
不过这句话刚一出,人群中便立刻发出声声哄笑。
尚随清还是那副笑模样,只不过从包袱中拿出一枚蜂窝煤,放在装满水的铜锅下点燃,朗声道:“诸位请看,小子可以保证讲完如何做出取暖之物,此水仍沸。”
众人看他自信的样子,心中也忍不住生疑。
看看吧,看看又不要钱。
况且,如果是真的呢?眼看着天越来越冷,要是家中日日有碳烧,想想都是件眼热的事。
存着这样的心思,尚随清身侧围了不少人。
她心里也长舒一口气,终于放下了压在心里的石头,她不怕留不下人,就怕没人来看。
“七成煤与三成黄泥,用特定器具塑成形,太阳下晒干即可。”尚随清东西准备的齐全,话音刚落又拿出模具细细给大家讲解。
那模具造型简单,原理也不算太难,不少有点手艺的人潦潦听几耳朵便明白了其中奥义。
那蜂窝煤在特制的小炉里烧得通红,热量稳定而持久,远比寻常柴薪耐烧,成本却低得令人咋舌。
围观的人群从好奇到震惊。
她站在融融热源旁,沸腾的水汽往上冒,又吸引了更多人驻足。
尚随清清朗的声音传遍小巷:“此物制法简单,不为牟利,只为让更多人能熬过这寒冬。有愿学者,皆可来此,分文不取。”
“好!”
一个清越的声音自身后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