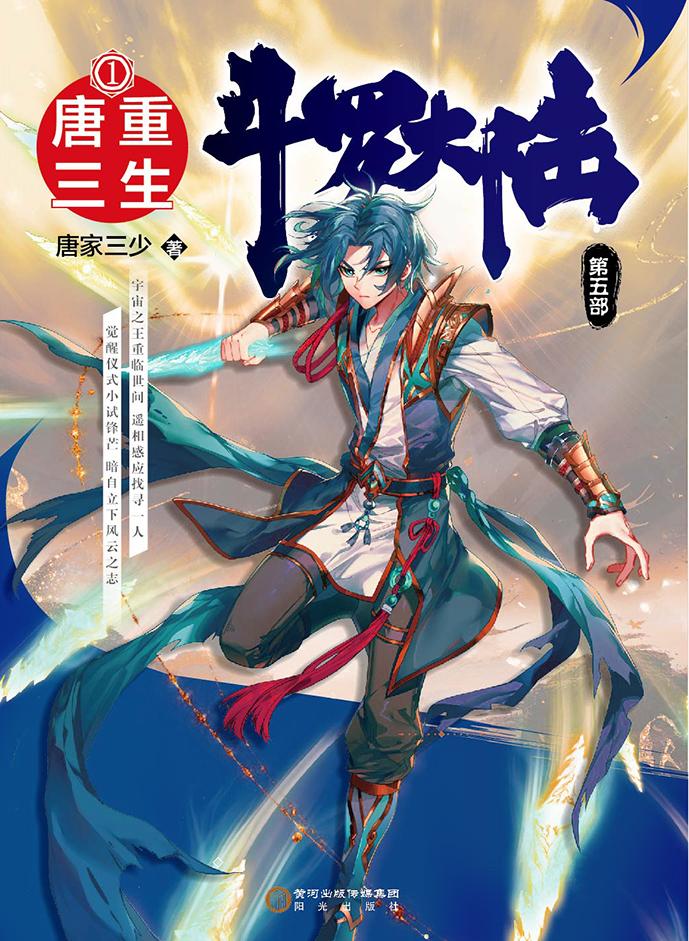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死敌总想和我官宣免费 > 补昨日更新明日照常更(第1页)
补昨日更新明日照常更(第1页)
尚随清一人在室中,伏案外衫披在身上,信纸展平,她人长得清俊秀气但字却洒脱恣意,写完后便从怀中掏出印章,在印泥上揉着均匀朱色。
红色的章印刚刚摁在纸面,她的房门口便吵吵嚷嚷,一阵比一阵高的声音呼着她。
“先生!”
“先生!”
尚随清抬手把外衫穿上,推开门:“什么事?”
学子群中窃窃私语半晌,却无人敢出来。
尚随清平时虽然脾气不坏,但立威颇深,大家都畏惧也尊敬这位年纪轻轻却支撑起学堂一切开支的先生。
“学堂来新人可以。”
武邑被诸位学子从人群中推出来,一个踉跄,却还是先作了个狼狈的揖道:“但这两个小女娃不行。”
是指前日的在学堂门口的那位妇人和两个女儿。
风卷进来,尚随清抬手拢紧衣襟,她不语,用眼神示意他继续,等着他把自己的理由都说出来。
那日她觉得那两个女孩子还是该去上学的年龄,于是随口让管仪安排了下去。
她们之前都游走在乡下田野里,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家都是贫苦出身,并非是自视清高,瞧不起人,只是如今我们一群男儿与她们同堂,她们日后的名声该如何?”
武邑的声音越来越低,最终声音被彻底掐灭在嗓子眼里。
他家中也有姐妹,知道好名声对她们以后的重要性。
武邑小心翼翼抬眼看向尚随清的脸色,先生一向不喜更改自己的意见,可这次他没等来尚随清有什么表态,只是看她抬手疲惫一遮眼。
是了。
这次确实是她欠考虑。
“我会考虑,你们先回去早早休息吧。”尚随清朝他们一挥手道。
他们还想说什么却都被尚随清挡了回去,于是只能齐齐告退:“是,先生。”
尚随清重回房中,她把那封信又重读了一遍那封信,犹豫地又在信上又添了几笔,塞进小小的信匣中准备明日寄出。
半年前,她重回京城,有父亲的先例在前,开办学堂她也是慎之又慎,只有一个底线,不触犯世家利益。
于是她就不欲在学堂中开办科举范畴中的科目,而是面向百姓开办木工、厨艺诸如此类的技术科。
但当时接手的学堂时候,秩光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保留教授四书五经的科目。
“你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不读书不明智,你的想法就是空想。”秩光奚信誓旦旦道。
况且当时学堂的情况也不允许。
眼下有了元疆饶的资助,学堂情况好了很多,尚随清也便把此事提上进程。
她等着对面那两人的回信。
元疆饶一人独坐府中。
自从那日两人在府中会宴之后,元疆饶所谓府邸年久失修,无处可去的蹩脚理由就再也立不住脚。
尚随清就把他赶回了府中。
丝毫不留情面。
元疆饶站在尚随清房门前道:“好歹我与尚大人还有几夜之情,何必如此。”
他故意说些引人误会的话,却十分刻意地把挑衅的眼神扔给管仪。
管仪支了张摇椅坐在院中看着他们两人拉扯,笑而不语,哪怕接受到了元疆饶的挑衅眼神,也只是气定神闲抿了一口茶。
她虚虚做了个口型。
“妾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