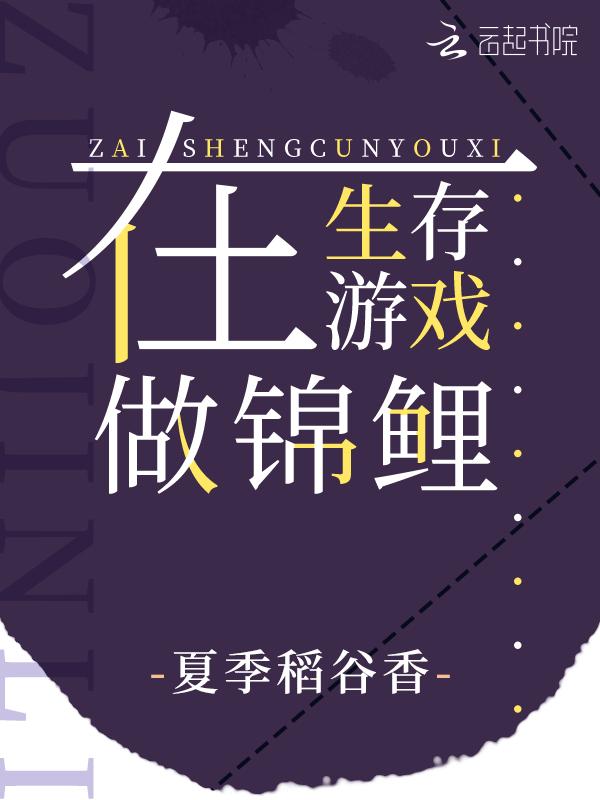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重生后夫君搂着我 > 24第 24 章(第2页)
24第 24 章(第2页)
“谁说写一百遍了。”江淮锦有点着急:“山长只罚我写五十遍,又没有罚你。我们只要写够五十遍就可以。”
“哦,那你就好好写,正好练练你的字。”
“顾瞻!”江淮锦急得过去推搡他:“我才不要写这个,你帮我写。”
“不就是个戒律,有什么不能写的?”顾瞻不懂。
“因为……”江淮锦正要开口,忽地顿住,继续而脸颊通红,直接背过去哼了一声:“反正你写,我不写。”
戒律没什么不能写的,江淮锦也不是没有被罚过。前世他混不吝爱玩闹,尤其跟顾瞻新成婚的时候,没少折腾顾瞻,有时候闹得实在有些过,被宫里的皇帝舅舅知道就罚他抄戒律,陛下罚得重江淮锦抄得头疼,每日点灯熬夜地写,被顾瞻那厮知道以后,好一顿嘲笑。
气得江淮锦没忍住跟他在书房打了一架,在顾瞻的脖子上面咬出来好几个牙印,打那以后顾瞻就给了他承诺,凡是江淮锦的惩罚他顾瞻都担着,往后再不会让他来抄这些东西,才算哄得江淮锦消气。
不管时光如何流转,顾瞻的承诺从来不会食言。
所以,就得顾瞻写!
“那、那大不了就你写戒律,我可以默写论语还有你新给我讲的诗经。”江淮锦想了想还是决定让步一点,他不能在顾瞻面前表现得太蛮横:“总比抄戒律有用吧?好不好?”
撒娇一向管用。江淮锦趴在桌子上偷偷去瞄板着脸抄写戒律的顾瞻,实在没忍住自己低头笑了起来,却不成想让顾瞻抓了个正着,给了他一个警告:“一会儿我检查要是错一个字,一个字十遍!”
“嗯嗯嗯,好好写呢。”江淮锦的嘴角上扬。
真好,他喜欢这种可以跟顾瞻在一个桌子上写东西的感觉,当然,如果顾瞻可以抱着他的话,那就更好了,不过不着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着急吃不了热豆腐。
抄写对顾瞻来说并不费什么功夫,为难人的是晚上的就寝。
本来以为山长已经给他特殊照顾,并不会真的就实打实关这小公子的禁闭,多半夜深以后就放人归家,不然人家那个当官的舅舅问起来,也不好交代不是?顾瞻是这样以为的,可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睡觉了,你怎么不上|床?”江淮锦已经宽衣,只着里面单薄的素色锦衣,趴在床上盯着顾瞻看:“不写了,明天再写,实在写不完就算了,我去跟山长说。”
顾瞻没抬头:“你先睡。”
“我等你。”
顾瞻攥紧了手上的笔,墨汁滴下来弄脏了他刚写的字,压着声音又重复一遍:“你快点睡。”
“说了等你。”江淮锦半点不在意,自己拿着一本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杂记仰躺回去:“快点来给我讲这个吧,这个好有意思,好像是一本游记,你说真的有地方会有这种长得像鹿又像马的东西吗?还有这个巫蛊是什么呀?人中了巫蛊会死吗?哎呦,好疼!”
碎碎念忽然被惊呼声打断,顾瞻扔了笔大步过来,见江淮锦捂着脑袋一脸痛色,拧眉:“怎么回事儿?磕着头了?我看看。”
“发冠上的这个东西扎我。”江淮锦扯了扯发冠上的玉笔,扯了两下没扯动,反而扯乱了头发。
顾瞻拿开他的手,过去帮忙拆发冠:“睡觉知道脱衣服怎么不知道取掉这玩意儿。”
江淮锦嘟囔着:“你写写就不管我,我在等你呀。”
“好了。”拆掉发冠理顺了头发,顾瞻正要起身,就被江淮锦一把拉住:“睡觉了,你还干什么去?吹蜡烛,我好困。”
顾瞻深呼一口气:“这床太小,你自己睡,我打地铺就行。”
“打地铺?”江淮锦眨了眨眼睛,像是没理解顾瞻,但又好像有点理解,半晌才磕磕巴巴地说道:“可、可是地上凉,你不能睡地上。我们挨着睡没关系的。”
话说这样说的,可说话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小,乃至最后自己都不敢再去看顾瞻,耳垂也隐隐约约透着粉意。
虽说,可顾瞻又不一样,江淮锦往里面挪了挪给顾瞻腾位置:“上来睡吧,不要冻着万一生病怎么办?”
顾瞻转身,就看见江淮锦乖乖缩在靠墙的位置,抿着嘴唇视线也不敢跟他对上,紧张得那么明显,脸上的粉|嫩藏都藏不住,顾瞻盯着看了一瞬,直接欺身过去,压住辈子按住了江淮锦的手腕,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在江淮锦耳边低声道:“可床这样小,我夜里睡相又不好,万一压到你怎么办?”
热意扑面而来,全是顾瞻的气息,江淮锦整个人好像被顾瞻裹在怀里,他的呼吸有点急促,心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好像下一刻就要跳出来,跳到顾瞻怀里去,江淮锦想伸手按住它,可他的手腕被顾瞻按住,动弹不得。
“看,你都热出汗了。”顾瞻的手指在江淮锦鬓角轻轻拂过,语气轻到好似漫不经心:“这样怎么能一起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