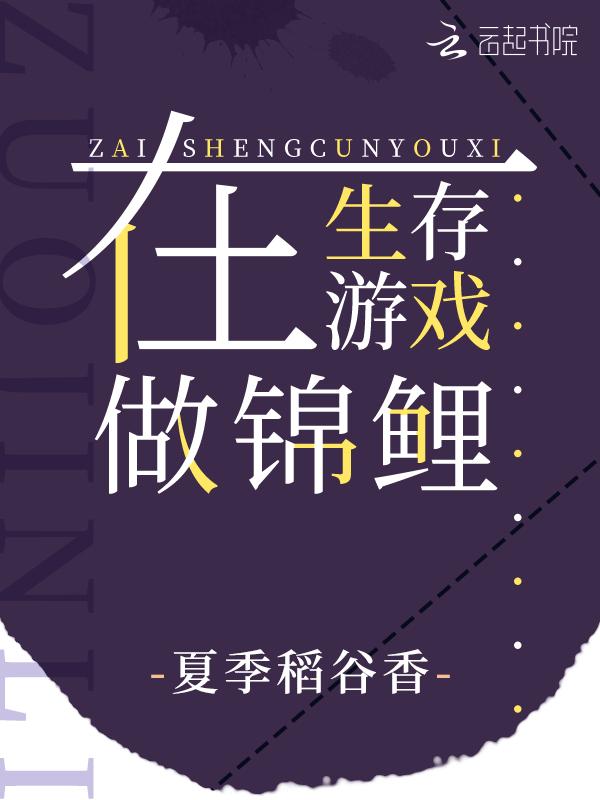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北宋小农民 > 19第 19 章 军令状(第3页)
19第 19 章 军令状(第3页)
赵燕直脸上的笑意倏地一收,眼神瞬间冷冽如冰:“既然看到了,便听我令谕。
祭礼在即,各部当以此幡为鉴,凡祭礼所用之物,无论器皿、仪仗、服幔、陈设,但有丝毫污损、陈旧、不合规制之处,自行检视,即刻修补更换。
我不管你们往日如何惯例,此番祭礼,关乎圣心,关乎国体,绝不容半分敷衍亵渎,若待我明日查检出来,休怪我按大不敬之罪,先斩后奏。”
最后四个字,如同冰锥,狠狠刺入在场每个人心底。那些原本还存着侥幸,想着糊弄过关的小吏内侍,无不脸色煞白。
赵燕直不再看他们,目光重新落回王教习和琼环二人,语气复又温和:“王教习手伤未愈,此番辛劳,我记下了。唐家娘子们年少有为,更当嘉奖。”
他身后的禁军护卫立刻上前。
“赏绣艺坊王教习白银二十两,上等伤药两瓶。赏唐家娘子白银各十两,以资嘉勉。”
三人躬身行礼:“谢主祭赏赐。”
赵燕直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院门外。
李检校尖着嗓子,气急败坏地吼道:“都聋了吗?没听见主祭的话?还不快滚去清查自己手里的东西,办不好的,仔细你们的脑袋。”
吼完,他自己也脚步匆匆地走了,显然是去处理自己可能存在的疏漏。
王教习将赏银和伤药小心收好,哑声道:“唐照环,唐照琼,你们自去歇着,后面的事,我交别人去忙。”
祭礼前一日,深夜,监理太监李检校的值房。
“检校,您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位主祭爷也太难伺候了吧。”一个管器皿的内侍苦着脸抱怨,“往常哪有这般折腾,大体上过得去不就行了。这位爷倒好,拿个破幡帐小题大做,如今更逼得大伙儿像没头苍蝇似的。库房那边光清点替换有锈迹的铜灯座就忙到后半夜,要人命了。”
“就是。”另一个管仪仗的小吏接口,“咱们这皇陵供奉,风吹日晒的,哪能件件都跟新的一样,往年不都这么过来了?偏生这位爷眼里揉不得沙子,非拿着鸡毛当令箭,在咱们这儿抖威风。”
众人七嘴八舌,怨气冲天。
李检校慢条斯理地呷了口茶,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听众人抱怨完了,他放下茶盏,嗤笑一声:“行了行了,都消停点。该查查,该补补,熬过明日祭礼,天大的事也了了。”
他环视一圈,面上是看透世事的精明和冷漠。
“这位爷,姓赵没错,是宗室也没错。可从他爹起,就跟今上出了五服。
按咱大宋的规矩,宗室无旨不得出京,不得为官,不得从军,不得经商,王爷也就名头好听,领份俸禄罢了,实权半点也无。
这位郎君,走了天大的运气才捞着这次主祭的机会,他若把祭礼办得平平无奇,或是出了岔子,怕是连他爷那点恩宠都要耗尽了。
所以他才这般较真,处处显摆他的用心,纯孝,想在官家面前露脸,给自己搏个前程。”
“那咱们就这么被他当猴耍?被他逼死?”有人不服气。
“反正就剩最后一日了。”李检校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祭礼一过,他乖乖回汴京继续当他的富贵闲人。这地界儿,还是咱们说了算。水至清则无鱼,这道理,上面的人比咱们更明白。”
他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都打起精神,他想要面子,咱们就给他把面子做足。只要祭礼顺顺当当结束,自有你们的好处,懂吗?”
值房里响起几声应和。
“懂。”
“听检校的准没错。”
李检校满意地点点头,挥了挥手:“散了散了,该干嘛干嘛去。仔细点,别在最后关头撞到那位活阎王手里。”
众人纷纷告退,打起精神去应付那宗室边缘人最后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