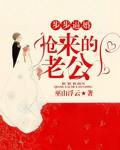奇书网>大明神医 > 第107章 船厂匠户现分歧 实学士子起风波(第2页)
第107章 船厂匠户现分歧 实学士子起风波(第2页)
“今日开学,咱们不谈圣贤言,只论万物理。”林奇拿起一根木尺,站在木板前,“大家看,这根木棍,为什么能让一个孩童,撬动比他重十倍的石块?”
生徒们瞬间炸了锅——来自官学的生员们面面相觑,有人小声嘀咕:“这不是匠人用的法子吗?怎么搬上讲堂了?简首是奇技淫巧!”而工匠子弟们则瞪大了眼睛,凑到木板前仔细观察,脸上满是兴奋——他们在家中见父亲用过类似的法子,却从没想过其中还有“道理”。
林奇听到了嘀咕声,却不以为意。他用木尺演示着杠杆的原理,从“省力”“费力”讲到力臂与重量的关系,还引申到战场上的投石机、农田里的水车,甚至日常用的剪刀、筷子。原本不屑的官学生员们,听着听着也入了神——他们第一次发现,这些“匠作之术”里,竟然也藏着如此精妙的逻辑。
实学院的课程设置更是大胆:上午学习《论语》《中庸》等基础经义(这是朱标坚持的底线,为了避免被指责“背离传统”),下午则按兴趣分科,学习算学(从加减乘除到几何测量)、基础格物(讲解声光热力的简单原理)、农政概要(介绍新作物种植、水利知识),甚至还有商事初步(讲解记账、贸易规则)。
教习的选择也打破常规:除了聘请三位不得志的老翰林讲授经义,更多是来自工部的技术官员(讲格物、农政)、钦天监的算师(讲算学),甚至还有民间的老木匠、老农夫(现场演示器物制作、作物种植)。
国子监弹劾,舆情汹汹
实学院这种“离经叛道”的教学模式,很快在京城士林掀起了轩然大波。国子监内,几位资深博士聚在一处,提起实学院便满脸愤慨。
“成何体统!”一位姓刘的博士拍着桌子,气得胡须发抖,“让匠人之子与读书人同堂就学,己是辱没斯文!如今竟将‘算学’‘匠术’搬入学堂,与圣贤书并列,简首是骇人听闻!这是要把天下读书人都教成匠人吗?”
“还有那林奇!竟敢曲解‘格物致知’!圣人说的‘格物’,是探究事物之理以明道德,他倒好,用来讲什么‘杠杆’‘浮力’,纯粹是坏人心术,动摇国本!”另一位博士附和道,语气中满是鄙夷。
“必须上奏朝廷!请求陛下取缔这等不伦不类之所,严惩误导学子的林奇!否则,大明学风败坏,后患无穷!”
短短几日,几份措辞激烈的奏本就送到了通政司,核心内容无非是弹劾实学院“混淆士农工商之序”“违背圣贤教化”“恐引学风败坏”,要求朝廷立刻关闭书院。
东宫应对,以实绩定成败
东宫书房内,朱标将弹劾奏本递给林奇,眉头微蹙:“林先生,阻力比预想的来得更快,言辞也更激烈。几位老臣还在朝堂上公开质疑,父皇虽然没表态,但脸色不太好看。”
林奇快速浏览完奏本,放下纸张,神色依旧平静:“殿下,他们急了。”
“哦?为何?”朱标有些疑惑。
“因为他们感觉到了威胁。”林奇解释道,“实学院若成功,培养出的人才,既能通晓经义,又精通实务,将来在治理河工、修建水利、管理贸易等事务上,会比只会八股的官员更有用,必然会受到朝廷重用。这就打破了他们靠‘科举经义’垄断学问和仕途的局面——他们骂得越凶,越证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朱标沉吟片刻,还是有些担忧:“话虽如此,但舆情汹汹,父皇那边若施压,怎么办?”
“殿下,还记得北伐前的争论吗?”林奇提醒道,“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用新火器、新战法,结果呢?事实胜于雄辩。对付这些质疑,最好的办法不是争辩,而是用实绩说话。”
他顿了顿,提出建议:“请殿下给实学院半年时间。半年后,咱们邀请翰林院、国子监的官员,亲自来书院考较生徒——既考经义,也考算学、格物。若生徒们连基本经义都荒废了,臣自愿请罪,关闭书院;若他们不仅经义未废,还能在实务学问上展现出真本事,甚至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计算堤坝尺寸、设计简单农具),那便是实学院价值的最好证明,到时候,再想质疑,也没人能说什么了。”
朱标眼睛一亮,瞬间明白了林奇的用意——这是用“结果”堵上所有人的嘴。他立刻点头:“好!就依先生之言!孤这就去见父皇,把考较的时间定在半年之后。这半年内,孤会顶住压力,不让他们再乱提弹劾!”
一场关于教育理念的较量,就此拉开帷幕。而龙江船厂的那艘宝船,也在争议与期待中,一天天露出雏形。大明的改革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但每一步,都朝着更广阔的未来迈进。
(第107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