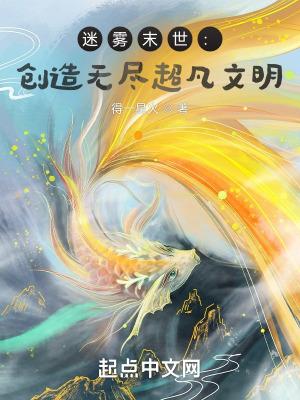奇书网>偏执太子驯狼记by笔趣阁免费阅读无弹窗 > 第46章(第2页)
第46章(第2页)
“苏雯是谁?”
裴既白突然开口,声音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流。车窗外的阳光照进来,为他侧脸镀上冰冷的釉色。
严燊后背一凉,有种被毒蛇盯上的错觉:“什么苏雯?”
“昨晚你喊的名字。”裴既白的指节在真皮座椅上敲出危险的节奏。
“我不认识——”
“苏微?”裴既白眯起眼,周身气压又低了几分。
严燊愣了几秒,突然忍不住低笑出声,胸腔震动带动喉结滚动:“是suvi。”
裴既白指尖一顿,隐约记起昨晚这人确实大着舌头嘟囔过什么——那些破碎的音节在酒气中扭曲,时而像苏雯,时而似苏微,最后都融化在哽咽的尾音里。
“一条狗。”严燊面不改色的回答,“两年前就死了。”
裴既白的表情微妙地松动了一瞬,他还以为是严燊某个忘不掉的白月光。
严燊不知道昨夜为何会梦见suvi。那是刚上初中那年,母亲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只毛色油亮的德牧幼犬,甚至比严小雨还要早来到这个家。
他永远记得那个盛夏午后,母亲蹲在院子里,手指轻抚着小狗柔软的耳尖:“就叫suvi吧。”她的笑容比阳光还暖,“在芬兰语里,是夏天的意思。”
可严燊不喜欢狗。
自从suvi为保护小雨被活活打死在后巷,他就再也没碰过任何宠物。
当黑色宾利稳稳停在大厦前,裴既白侧目看向身旁的男人。
晨光透过车窗,在严燊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斑驳树影——那双眼睛依旧如深潭般平静无波,薄唇抿成一道冷硬的直线。
裴既白太熟悉这种表情了。
严燊就像一匹被强行套上鞍辔的野狼,即便收敛了利齿,骨子里的野性仍在血液里沸腾。
如果不是为了严小雨,这个男人恐怕连一个眼神都吝于给予任何人。
他们之间始终横亘着无形的天堑——一个是金尊玉贵的世家继承人,一个是泥潭里摸爬滚打的亡命之徒。
就像此刻,严燊为他拉开车门的动作标准得无可挑剔,可那绷紧的下颌线却泄露了压抑的不甘。
正午的阳光毒辣得刺眼。
裴既白迈出车门时,热浪裹挟着汽车尾气扑面而来。
几个西装革履的职员匆匆擦肩而过。
远处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晃得人眼花,更远处某栋大厦的天台上,一道金属反光一闪而逝。
严燊突然绷紧背脊,本能地朝反光方向望去。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
“小心!”
严燊的暴喝与玻璃碎裂声同时炸响。裴既白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后背重重撞在车身上。严燊整个人覆在他上方,子弹擦着他们耳畔呼啸而过。
人群瞬间炸开锅。
在混乱的尖叫声中,一个男人突然从身后冲了上来。他长相普通得得令人过目即忘,或许上一秒还与自己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