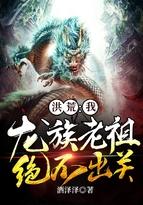奇书网>战魂铭人紫昙 > 第172章 寒门崛起(第1页)
第172章 寒门崛起(第1页)
青阳城的朱雀大街,从未如此热闹过。
晨光刚洒上榜单的红绸,这里就己挤得水泄不通。寒门子弟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袍,踮着脚尖,伸长脖子,目光死死盯着那张贴在城墙上的黄榜——那是青阳国首批科举的放榜名单,墨迹未干,却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
“出来了!放榜了!”
随着礼官一声高喊,两名士兵缓缓扯下红绸,黄榜上的名字赫然映入眼帘。
“经义科第一,苏文!”
“军务科第一,秦武!”
“算术科第一,周明!”
人群中爆发出震天的欢呼。一个穿着粗布长衫、面容清瘦的青年猛地攥紧了拳头,眼中瞬间涌满泪水——他就是苏文,一个靠抄书为生的寒门士子,此刻他的名字,正端端正正地排在经义科的榜首。
“苏大哥!你中了!中了第一!”旁边一个少年激动地摇晃着他的胳膊,那是他的同乡,这次也考中了算术科的第五名。
苏文用力点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布满补丁的衣襟上。他想起了早逝的父母,想起了寒窗十年的苦读,想起了那些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世家子弟——今天,他终于用笔墨证明了自己。
不远处,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汉子也盯着榜单,军务科第一的“秦武”二字,让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他曾是军中的一名普通伍长,因识字被推荐参加科举,没想到竟拔得头筹。
“秦大哥!以后就是秦大人了!”同来的士兵拍着他的肩膀,又羡慕又激动。
秦武挠了挠头,嘿嘿一笑:“还不是托大王的福,给了我们这些粗人机会。”
黄榜前,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中榜的寒门子弟或相拥而泣,或跪地叩谢,或与同乡击掌相庆;落榜的虽有失落,却也眼中闪烁着希望——至少,他们看到了一条可行的路,明年还能再来。
围观的百姓们也纷纷叫好,指着榜单上的名字议论:
“苏文我认识!就是那个在书铺抄书的后生,学问好得很!”
“秦武是俺们村的!小时候还跟俺一起放过牛呢,没想到成了大人!”
“大王说了,以后不管出身,有本事就能当官,这才是好世道啊!”
欢呼声、议论声汇成一股洪流,在朱雀大街上涌动,充满了向上的朝气。这股朝气,比任何庆典都更能彰显青阳国的新生。
三日后,明德殿。
林浩坐在龙椅上,目光扫过阶下的十名新科官员。他们穿着统一的青色官袍,虽略显拘谨,却个个眼神明亮,透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苏文站在最前面,身姿挺拔,秦武则微微握拳,带着军人的硬朗。
“诸位都是我青阳国首批科举选出的人才,”林浩的声音温和却有力,“朕不拘一格降人才,为的就是让你们这些有才干、知民间疾苦的人,能为百姓办实事,为青阳谋发展。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
苏文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躬身道:“大王,臣以为,当前首要之事,是安抚新收的西陲三城和南境两镇百姓。这些地方刚经历战火,又换了领主,民心不稳。臣恳请大王,减免这些地方三年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
他的声音清晰洪亮,条理分明,丝毫不见初次上殿的怯懦。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你说得有理。新收之地,当以安抚为主。传朕旨意,西陲三城、南境两镇,三年内免征赋税,由国库拨款,帮助百姓重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