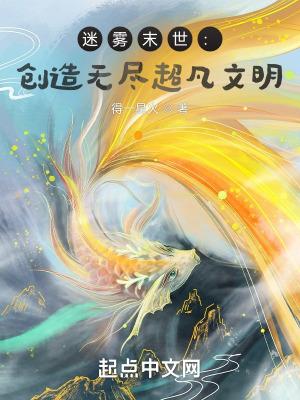奇书网>所有执念 > 第46章 踏上旅程寻线索(第2页)
第46章 踏上旅程寻线索(第2页)
她盯着那行字,心跳慢了一拍。
这不是遗物的随意埋藏,是有人刻意留下线索。
她把塑料片收进笔记本夹层,重新靠回墙边。雾己经淹没了大半个驿站,远处的山影彻底消失。她知道不能再往前走了——今晚的感知己经接近极限,再强行深入,可能会被残魂的执念反噬。
她闭眼休息,手指无意识着笔记本封面。帆布粗糙,边缘有些磨损。她想起出发前,租客把铜铃放进包里的动作。他没解释,也没多说,只是让她记得自己为何出发。
她现在明白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寻人。老兵弟弟的执念没有散,是因为有话没说完,有事没做完。而那句话,可能就卡在东室的通讯中断那一刻。
她睁开眼,看向东侧断墙。
风穿过残破的窗框,发出低微的呜咽。她没再试图去听更多,只是把笔记本收好,站起身。腿有些发麻,她活动了一下,背起包。
铜铃再没响过。
但她己经不需要它立刻回应。
她知道方向是对的。
她开始往回走,沿着来时的小径。雾在身后合拢,淹没驿站的轮廓。走到半路,她停下,从包里取出地图,在月光下确认位置。她用笔在“废弃驿站”旁边画了个圈,写下:“残魂痕迹确认,水壶与塑料片为证,东室为关键点。”
然后,她撕下这一页,折好,放进侧袋。
剩下的两处红圈,还在地图上等着。
她把地图收进包,继续往前。脚下的路开始下坡,通往山外的公路。远处,隐约有车灯的光亮。
她没加快脚步,也没回头。
走到公路边,她站在路边,等下一班车。风从山口吹来,带着湿冷的土腥味。她把包抱在胸前,手插在侧袋里,指尖触到铜铃的边缘。
它还是冷的。
但她掌心是暖的。
一辆货车从远处驶来,车灯扫过她的脸。她没动,首到那光过去。
站牌锈迹斑斑,时刻表上的字迹模糊。她没看,只是站着。
包里的铜铃,忽然轻轻颤了一下。
不是震动,也不是响动,而是一种存在感的回归,像心跳重新被听见。
她低头,手还在侧袋里。
铃身贴着布料,安静地躺着。
她没把它拿出来,只是收紧了手指。
远处,又一束车灯亮起,缓缓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