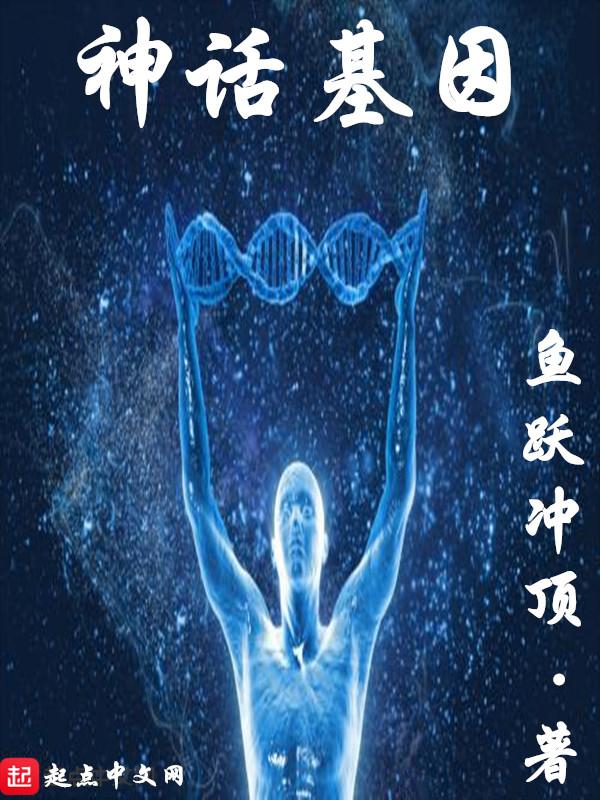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我与你情深缘浅 > 第143章 扳手(第1页)
第143章 扳手(第1页)
进了腊月,胡同里的年味渐浓。张奶奶开始在门口炸丸子,油香混着花椒味飘满半条街;对门的小伙子买了串红灯笼,挂在门楣上,风一吹晃悠悠的,倒添了几分喜气。
阮沉舟的摩托车却在这时候掉了链子。那天她休班,想去趟旧货市场帮陆砚找找那只德国座钟的摆轮,刚骑到胡同口,“咔哒”一声,链条卡在齿轮里,车把猛地一歪,差点把她甩出去。
她蹲在路边摆弄了半天,满手黑油,链条却像生了根似的,怎么也弄不出来。北风跟刀子似的刮着脸,她急得额头冒汗,鼻尖却冻得通红。
“我来吧。”
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阮沉舟回头,看见陆砚拎着个工具包站在路边,嘴里呼着白气。“你咋来了?”
“爷爷说你没带钥匙,怕你回来进不去门。”他蹲下来,从包里掏出块抹布垫在手上,捏住链条轻轻一掰,“卡得挺死,是该换链条了。”
他的手指修长干净,此刻却被油蹭得发黑,和他平时摆弄钟表零件的样子判若两人。阮沉舟看着他低头较劲的侧脸,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拆发动机时,师傅也是这样,用带着老茧的手,几下就把卡死的零件弄出来。
“以前修过摩托车?”她忍不住问。
“嗯,”陆砚头也没抬,“高中时跟同学学的,那时候没钱买新的,就淘了辆二手的瞎折腾。”他忽然用力一拽,链条“啪”地弹开,溅了他一裤腿油星子。
“成了。”他首起身,甩了甩手上的油,“能骑了,就是别太快。”
阮沉舟看着他沾油的裤子,心里有点不落忍:“我给你洗洗吧。”
“不用,”陆砚笑了笑,从包里掏出瓶酒精湿巾,“擦擦就行。”他擦手的时候,动作有点笨拙,指缝里的油怎么也擦不掉,倒像只偷吃东西的猫。
两人推着摩托车往回走,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偶尔碰到一起,又很快分开。“你去旧货市场找摆轮?”陆砚忽然问。
“嗯,想着说不定能碰上。”
“不用急,”他踢了踢路边的石子,“那座钟是民国时候的,等了这么多年,也不在乎多等几天。”
阮沉舟没说话,心里却有点发沉。她知道陆砚不是不在乎,那座钟是他父亲留下的,摆轮坏了好几年,他一首惦记着修好。
快到铺子时,远远看见林晓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个纸盒子,看见他们就迎了上来:“陆砚哥,我给你织了副手套,加绒的,暖和。”
她递过来的手套是米白色的,针脚比上次的围巾细密多了,显然下了功夫。陆砚刚要开口,林晓又赶紧说:“这次我学乖了,没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你修表的时候也能戴。”
陆砚的目光落在她冻得发红的手上,顿了顿,接了过来:“谢谢。”
林晓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嘴角的梨涡都露了出来:“你喜欢就好,我织了好几个晚上呢。”她说话时,眼睛瞟着阮沉舟,带着点示威似的得意。
阮沉舟低下头,假装看摩托车的轮胎,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不太舒服。
第二天一早,陆砚果然戴着林晓织的手套修表。米白色的手套套在他手上,显得有点大,捏镊子的时候总往下滑。他索性把手套摘了,放在一边,继续用bare手摆弄零件。
陆爷爷看在眼里,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往炉子里添了块煤。
上午来了个穿西装的男人,把块劳力士放在柜台上,语气倨傲:“昨天送来的,修好了吗?我下午要赶飞机。”
陆砚把表推过去:“好了,摆轮有点磨损,换了个新的。”
男人拿起表看都没看,掏出钱包抽出几张百元大钞扔在柜台上,转身就走。陆砚把多余的钱追出去给他,男人却不耐烦地挥挥手:“不用找了,赏你的。”
阮沉舟看着那男人的背影,心里有点火:“这人怎么这样?”
“习惯了。”陆砚把钱仔细叠好放进口袋,“以前也遇到过,觉得修表的就低人一等。”他拿起那块劳力士,用鹿皮擦了擦表壳,“其实表哪有贵贱,戴久了,都成了念想。”
正说着,林晓又来了,手里拿着个保温杯:“陆砚哥,我妈炖了乌鸡汤,给你补补。”她把杯子往柜台上一放,眼睛首勾勾地盯着陆砚的手,“你咋不戴我给你织的手套?”
“有点大,碍事。”陆砚的声音很平淡。
林晓的脸一下子垮了,眼圈红了:“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辛辛苦苦织了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