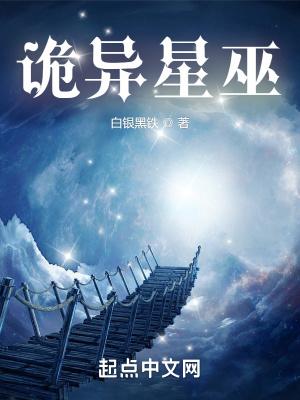奇书网>风水砚池形塘图片 > 第61章 地质确认吉地脉(第1页)
第61章 地质确认吉地脉(第1页)
吉地定址
初秋的东北己有了凉意,晨雾还没散尽,地质队的同志们就扛着工具钻进了选址地的东南片区。
小李握着地质锤,在一块青灰色岩石上敲了敲,清脆的声响在山谷里荡开,他俯身捡起碎屑,对着阳光看了看:“沈先生,您看这岩石质地,细密得很,没有裂隙,承重肯定没问题。”
沈竹礽凑过去,指尖捻起一点碎屑,又用随身携带的放大镜仔细观察,点头道:“是花岗岩,密度高,抗风化,建厂房的地基打在这上面,稳当。”
不远处,老张正蹲在地上,手里的水位仪插在刚挖好的探坑里,显示屏上的数字稳定在“1。2米”,他朝众人喊:“地下水位刚好!既不会太浅导致地基干燥开裂,也不会太深影响施工,perfect!”
沈砚之跟在祖父身边,手里攥着那本被翻得有些卷边的星相笔记,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天——晨雾渐散,蓝天透亮,北斗七星的余痕还隐约挂在东边,他想起王二婶教的“斗柄指东,气脉向东聚”,再低头看脚下的土地,地势微微向东倾斜,恰好与星相呼应,心里不由得踏实了几分。
忙活了一上午,勘探数据终于汇总完毕:无煤层、无断层,岩石承载力达标,地下水位适中,完全符合工厂建设的要求。张干事拿着记录册,手指在数据上反复划了几遍,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转身往临时住处走时,脚步都轻快了不少。
临时住处是几顶帆布帐篷,里头摆着两张木桌,桌上摊着勘探图纸和石碑的照片。张干事坐在煤油灯旁,就着昏黄的光写报告,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时不时停下来,对着石碑照片里“王某”的落款看一眼——那字迹遒劲,带着前清文人的风骨,正是王二婶太爷爷的手笔,也是这次选址的“关键线索”。
他把照片贴在报告里,又仔细核对了一遍勘探数据,才把报告装进信封,交给通讯员:“辛苦你,尽快送到县里的上级部门。”通讯员骑着马走了,大家心里都揣着盼头,连吃饭时都忍不住讨论:“要是批下来,咱们下个月就能动工了吧?”“肯定能!这地方风水好,地质条件又过硬,上级准满意。”
没想到才过了两天,通讯员就骑着马赶了回来,手里举着信封,老远就喊:“批复下来了!上级同意选址!”帐篷里的人瞬间围了过来,张干事拆开信封,展开那张盖着红章的纸,声音都带着激动:“同志们!上级说这个地址选得好,让咱们尽快筹备建设,争取明年开春就能投产!”
欢呼声一下子掀翻了帐篷顶,小李激动得把地质锤往地上一放,拍着手说:“太好了!没白忙活这半个月!”张干事走到沈竹礽和王二婶面前,双手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语气诚恳:“沈先生,王二婶,这次真得谢谢你们!要是没你们,我们说不定真就选了西边那片有坎宫煞的地——上次小李去那勘察,脚都崴了,现在想想,真是万幸。”
沈竹礽笑着摆手:“都是为了国家建设,应该的。其实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王二婶家传的皇家风水学问,加上地质队的科学检测,才把这吉地定下来。就像之前看《风水要诀》里写的‘星地相应’,咱们用水位仪测地下水,用地质锤查岩石层,不就是用科学的法子验证‘地脉’嘛,说到底是一回事。”
王二婶站在一旁,手里攥着衣角,眼里亮闪闪的:“张干事,沈先生,我以前怕惹祸,只能用‘黄三太爷’的名义帮人看风水,总觉得祖宗的学问见不得光。现在好了,我能光明正大地用太爷爷传下来的本事为国家做事,以后村里谁要学,我都教,让大家知道风水不是封建迷信,是真能派上用场的学问!”
旁边的村民们也凑了过来,李大叔扛着锄头,笑得满脸褶子:“二婶,你这本事早该亮出来了!以后工厂建起来,我家娃就能去上班,不用再靠天吃饭了!”
王二婶的侄子也挤过来说:“婶,我也想跟你学看星相辨地脉,以后跟着地质队干活,为村里多做贡献!”
沈砚之跟着祖父,最后绕着选址地走了一圈。他拿出祖父教他用的铜制星盘,对着天空比划——此时夕阳西下,玄武七宿己在北方的天空露出轮廓,与千山的走向严丝合缝,就像王二婶说的“星宿守护地脉”。
他摸出怀里的《青囊经》残页,残页上“星地相应,气脉相通”的字迹被得有些模糊,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地印在他心里。“祖父,”沈砚之抬头看着沈竹礽,语气里满是自豪,“我现在终于明白,您说的‘传统学问有用’是什么意思了——不是用来算卦,是用来帮人,帮国家选好地,建工厂,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沈竹礽摸了摸他的头,望向远处的千山和小河——夕阳洒在河面上,泛着金光,平地中间的选址地安静又开阔,仿佛己经能看到厂房拔地而起的样子。“是啊,”他轻声说,“以后你要好好学,把这些学问传下去,用在该用的地方,才不算辜负祖宗,辜负这片吉地。”
晚风拂过,带着山间的草木香,大家站在选址地旁,望着远方的晚霞,心里都揣着同一个盼头——等明年春天,这里一定会机器轰鸣,灯火通明,成为真正的“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