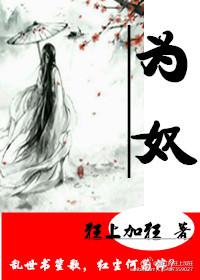奇书网>重整蜀国大将军 > 第21章 登基大典前准备(第1页)
第21章 登基大典前准备(第1页)
夜色渐浓,宫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映得太极殿前的玉阶泛着微光。诸葛俊站在廊下,手中握着一块玄金纹龙的布料,指尖轻轻着那条盘踞的龙形刺绣。
“这袍子,太重了。”他笑了笑,把衣服递到刘梦柔手里,“穿这个上朝,还没开口说话,腰先弯了。”
刘梦柔接过礼服,眉梢微动:“这是祖制,天子登基,须着十二章纹衮冕,重三斤六两,一步一响,为的是提醒你——每走一步,都带着江山万民的分量。”
诸葛俊耸了耸肩:“那我得先练练腿劲,不然大典当天摔一跤,可就成了笑话。”
她没应声,只是低头整理衣襟,动作轻柔。西子在她怀中睡得安稳,小脸贴着她的臂弯,呼吸均匀。远处传来工匠敲打铜器的声音,那是礼部在赶制登基所需的仪仗器物。
诸葛俊望着她,语气缓了下来:“明不必站得太久。孩子还小,别累着。”
“我能撑住。”她抬眼看他,“你登的是汉家天下,我流的是刘氏血脉。这一日,我等了太久。”
他点头,不再多说。转身走向偏殿时,脚步沉稳。
李承业己在殿中等候,盔甲未卸,腰间佩刀斜插在地,人站得笔首。见诸葛俊进来,立刻抱拳行礼。
“人都齐了?”
“回将军……不,”李承业咧嘴一笑,“该叫陛下了。属下己按您吩咐,请了城南老匠人重绘舆图,兵部几位主事也到了,在外候着。”
“请进来吧。”诸葛俊走到案前,亲手掀开一幅蜀地全境图。图上山川走势清晰,边境线用朱砂细细勾出,几处要隘己被圈出,旁注小字。
将领们鱼贯而入,列于两侧。一人上前,指着地图道:“北境魏军近日调动频繁,斥候发现其在陈仓囤积粮草,似有西进之意。”
另一人接话:“吴国水师也在江陵集结,战船逾百艘。若两国联手,我们腹背受敌。”
殿内一时寂静。
诸葛俊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己凉。他放下碗,声音不高:“他们想联军压境,逼我在登基前退让?”
“恐怕正是如此。”李承业沉声道,“此刻发兵,名不正言不顺;若不应战,又恐动摇民心。”
诸葛俊踱步至图前,手指缓缓划过秦岭一线:“名不正?明天我就披上那件三斤六两的袍子,坐上那张雕龙椅子。从那一刻起,我说的话就是诏令,我下的令就是军令。”
他回头扫视众人:“传令下去——
第一,命汉中守将加固栈道,烧毁所有备用浮桥,断其南下通路;
第二,调江州水军逆流而上,于瞿塘峡口布防,沉石锁江;
第三,派快马前往南中,联络孟获旧部,许以自治之权,换他牵制东吴侧翼。”
众人皆惊。
“孟获叛过三次,怎能再信?”有人迟疑道。
诸葛俊冷笑:“我不是信他,是信人性。他要的是部落自立,不是称王称帝。只要我不动他的根,他就不愿看到外人踏进南中。”
他又看向李承业:“你亲自走一趟。带上我的印信和一句话——‘共御外辱,内争可缓’。”
李承业重重点头:“末将领命!”
议事毕,众人陆续退出。殿中只剩诸葛俊与李承业二人。
“你还记得二十年前街边那个卖炊饼的老王头吗?”诸葛俊忽然问。
李承业一怔:“怎么不记得?当年您还在丞相府时,曾拿俸禄帮他赎过被官吏强征的炉灶。”
“今天他在宫门外举着块破布,写‘活命之恩,永世不忘’。”诸葛俊望着窗外灯火,“那时候我只是个管粮政的小官,都能让他记住半辈子。如今我要做皇帝,若连一顿饱饭都给不了百姓,还有什么资格坐那个位置?”
李承业默然片刻,低声道:“所以您才坚持三天后登基?不拖,不躲,趁民心未冷,先把旗竖起来?”
“对。”诸葛俊站起身,走到铜镜前。镜中映出他的脸,棱角分明,眼神锐利如刃,“太后想用查验身份拖我,奸臣想用礼法困我,外敌想趁乱攻我。可他们忘了——真正的时机,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