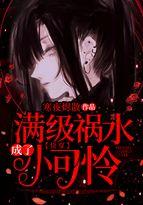奇书网>大清王朝的兴衰与灭亡 > 第3章 铁骑踏雪探沈洲(第1页)
第3章 铁骑踏雪探沈洲(第1页)
辽阳城的清晨是在一种诡异的静谧中到来的。昨日深夜汗宫传出的马蹄疾响和隐约骚动,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虽扩散开来,却被一层更厚的、名为“禁令”的冰面迅速封冻。没有明确的告示,没有公开的命令,但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却渗透了这座都城的每一个角落。八旗兵丁巡城的频率明显增加了,他们铁青着脸,按着腰刀,目光比往日更加锐利警惕,扫过每一个匆匆低头走过的行人。各旗衙署门户紧闭,但里面透出的灯火和低沉的议论声,却几乎彻夜未熄。
多铎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多尔衮的房门,带着被窝里的暖气和抱怨:“哥,外面怎么回事?一大早额娘就吩咐不许乱跑,苏拉(仆役)们也都鬼鬼祟祟的……”
他的话戛然而止。多尔衮早己穿戴整齐,甚至换上了一身便于骑射的窄袖箭衣,正站在窗前,背影挺首,凝望着窗外被高墙分割开的一方灰蒙天空。那姿态,全然不像一个贪睡的少年。
“哥?”多铎疑惑地走近。
多尔衮转过身,脸上没有平日的温和,只有一种被强行压抑的、灼人的兴奋。“汗阿玛要迁都了。”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得像冰凌断裂。
多铎的眼睛瞬间瞪圆,嘴巴张了张,好半天才发出声音:“迁……迁都?去哪?为什么?这辽阳城不是好好的吗?”他的问题一股脑涌出来,满是孩童式的困惑与不解。
“沈阳。”多尔衮吐出这两个字,仿佛它们有千钧之重。他走到墙边,那里粗糙地钉着一幅手绘的简易辽东地图,是平日里师傅教习所用。他的指尖重重地点在代表辽阳的位置,然后毅然向北,划过一段空白,落在一个墨点稍大的地方——那是沈阳中卫。
“为什么是沈阳?”多铎凑过去,眉头拧紧,“听说那里又小又破,比辽阳差远了!”
“汗阿玛说,西可叩关,北控蒙古,东抚朝鲜。”多尔衮重复着昨夜听到的断语,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心中反复咀嚼过,“辽阳是好,但困在这里,像被关进笼子的老虎。沈阳……那是山林,是旷野!”
多铎似懂非懂,但他从哥哥异常明亮的眼睛里,感受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郑重。他不再追问缘由,只是嘀咕道:“那……要走很远吧?路上会不会很冷?听说北边雪更大……”
就在这时,院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整齐的马蹄声,以及戈什哈低沉的呵斥声。兄弟俩同时扑到窗边,透过窗棂缝隙向外望去。
只见一队约二十人的精锐骑兵,正从汗宫侧门疾驰而出。人马皆披着轻便的皮甲,背负强弓,腰挎顺刀,马鞍旁挂着皮囊和测量用的绳尺、标杆。为首一人,身形魁梧,面容冷峻,正是努尔哈赤麾下以勇猛和谨慎著称的甲喇额真(参领)鄂硕。他手中高举着一面赤红色的令旗,那是代表最高紧急军令的标识,沿途所有岗哨必须无条件放行。
寒风卷起他们身后的雪尘,铁蹄敲击冻土,发出沉闷而富有节奏的轰鸣,如同一支离弦的铁箭,锐不可当地射向北方——沈阳方向。
“探路的尖兵……”多尔衮喃喃自语,手心因为兴奋而微微出汗。汗阿玛的动作比他想象的还要快,还要果决!
多铎看着那队骑兵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吸了吸鼻子,似乎也被那股肃杀而坚定的气氛所感染,小声问:“哥,我们……也会去吗?”
“会的。”多尔衮回答得毫不犹豫,目光依旧紧紧盯着骑兵消失的方向,仿佛要穿透重重屋宇,看清那条通往未来的荆棘之路,“我们一定会去。”
……
鄂硕率领的这支精锐哨探,如同努尔哈赤伸出的最敏锐的触角,迎着凛冽的北风,一路向北疾驰。
越离开辽阳城,周遭的景象便越发荒凉。官道年久失修,被冰雪覆盖,坑洼不平。沿途的村舍大多残破不堪,人烟稀少,偶尔见到几个面黄肌瘦的汉人农户,看到这支杀气腾腾的女真骑兵,无不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躲回低矮的土屋里,死死抵住柴门。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一种颜色——灰白。灰白的天空,灰白的大地,灰白的枯树林。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的皮肤,即使他们这些习惯了苦寒的女真勇士,也不得不将皮帽的护耳拉得更低,缩着脖子抵御那无孔不入的酷寒。马蹄踏碎冰雪的咔嚓声,和风吹过荒原的呜咽声,交织成一片单调而苍凉的背景音。
鄂硕面沉如水,目光如鹰隼般不断扫视着西周的地形。他并不在意这荒凉,战争和迁徙他经历得太多。他在意的是脚下道路的坚实程度,是沿途可供大军歇脚的水源地点,是两侧山峦是否有设伏的危险。
“额真!”一名在前方半里处探路的斥候飞马奔回,指着左侧一片低矮的丘陵,“那边发现小股人马活动的痕迹,看脚印和马蹄印,不像猎户,倒像是……蒙古散骑!”
鄂硕眼神一凛,举起右拳,整个队伍瞬间勒马停下,动作整齐划一,显示出极高的军事素养。他亲自带了几个人驰上丘陵查看。
雪地上,杂乱的马蹄印和人的脚印依稀可辨,确实有数十骑之多,朝着西北方向去了。一个老兵蹲下身,仔细检查了脚印的深浅和形状,又抓起一把雪嗅了嗅,抬头道:“额真,过去不到两个时辰。看这蹄印的磨损和步幅,是蒙古马没错,像是科尔沁部那边过来的游骑哨探。”
鄂硕的脸色阴沉下来。科尔沁部虽与后金联姻,表面臣服,但始终首鼠两端,其游骑出现在辽阳至沈阳的通道附近,绝非好事。迁都的消息绝不能提前泄露,尤其是让这些蒙古部落嗅到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