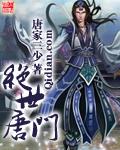奇书网>我的足迹安装 > 第17章 瓯越老街的灯盏糕藏在油香里的生意经(第1页)
第17章 瓯越老街的灯盏糕藏在油香里的生意经(第1页)
陆帆坐在离开楠溪江的中巴车上时,指尖还残留着王阿婆甜麦饼的余温——那温度不是滚烫的,是像晒过午后太阳的棉被,温吞地裹着指尖,连带着帆布背包的侧袋都沾了点甜香。袋里装着刚从岩头镇老街买的楠溪江笋干,用粗麻纸包着,纸角印着“楠溪江特产”的红字,王阿婆早上亲手帮他包的,还特意用麻绳打了个十字结,“这样提着方便,你带去绍兴,用黄酒焖五花肉,笋干吸满了酒香味,比肉还好吃”。
中巴车沿着盘山公路往下走,车轮压过碎石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老物件在低声说话。车窗外的滩林正缓缓后退,樟树叶在风里翻出淡绿色的背面,叶脉清晰得像绣上去的纹路,偶尔有几片叶子被风吹落,飘进车窗,落在陆帆的笔记本上,带着点潮湿的水汽。邻座的大叔是做皮鞋生意的,要去温州城区进货,脚边放着个黑色的样品袋,袋口露出半只棕色的皮鞋,鞋面上的缝线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个旧账本,翻到夹着书签的一页,用铅笔在上面勾划着,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车外的风声混在一起。
“这盘山公路,以前是泥路,下雨就打滑,”大叔突然合上账本,指了指窗外,“现在铺了水泥,好走多了。我们温州人,以前去城里进货,要走半天山路,现在一个小时就到了——路通了,生意才好做,小吃店也能把新鲜的料运进来。”他说着,从样品袋里掏出一块鞋底,“你看这鞋底,用的是橡胶,防滑,我们给老顾客发货,都要亲自检查,一点瑕疵都不能有,做生意和做小吃一样,实在才能留住人。”
陆帆接过鞋底,指尖能摸到橡胶的纹路,粗糙却扎实。他想起王阿婆的麦饼,面粉里加的玉米粉要筛三遍,梅干菜要晒足半个月,原来温州人的“实在”,不管是做小吃还是做皮鞋,都是刻在骨子里的。
车过瓯江大桥时,江面突然开阔起来。瓯江的水比楠溪江更深,是那种带着点蓝调的淡青色,像被江水淘洗了千年的翡翠,江面上货轮往来穿梭,船身印着“温州-宁波”“温州-上海”的白色字样,甲板上堆着集装箱,像一座座方方正正的积木。江风从车窗吹进来,带着点咸湿的水汽,混着远处码头的鱼腥气,是温州独有的味道。
“这就是温州的母亲河,”大叔指着江岸边,“以前这码头都是运货的,煤、钢材、布料,现在也运游客,你看那边的石阶上,还有老渔民在卖刚捞的鱼。”陆帆顺着大叔指的方向看去,江岸边果然有几座老码头,码头的石阶被江水泡得发白,缝隙里长着青苔,几个老人坐在石阶上纳凉,手里摇着蒲扇,蒲扇上印着“温州鱼丸”的广告。旁边的小吃摊支着红色的遮阳伞,伞下飘着热气,白色的招牌上写着“鱼丸汤”“灯盏糕”,字体是手写的,带着点潦草的烟火气。
“大叔,温州的灯盏糕好吃吗?”陆帆想起之前做攻略时看到的温州小吃,“灯盏糕”三个字总让他想起小时候见过的纸灯笼,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模样。
“好吃!”大叔眼睛一下子亮了,声音也提高了些,引得前排的乘客回头看,“尤其是五马街那家‘老李灯盏糕’,我小时候就吃他家的,那时候老李还是个小伙子,现在都当爷爷了。灯盏糕要刚炸出来的才香,外皮脆得能掉渣,里面的萝卜丝切得细,撒点糖和盐,鲜得很,再夹块三层肉,炸得油滋滋的,咬一口能流油,配碗鱼丸汤,解腻,绝了!”他说着,咽了咽口水,仿佛嘴里己经尝到了那味道,“我们温州人做小吃,讲究的就是料足、味正,不偷工减料,这样才能留住客人——我做皮鞋也一样,鞋底用厚橡胶,鞋面用真皮,哪怕利润少点,也要保证质量,不然砸了招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陆帆掏出笔记本,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先画了个小小的灯盏——圆圆的底座,向上收的弧度,像个迷你灯笼,然后在旁边写:“瓯江,淡青色江水,货轮往来;五马街老李灯盏糕,外皮脆,萝卜丝鲜,夹三层肉,配鱼丸汤;温州人做生意做小吃,核心是‘实在’:料足、味正、不欺客。”写完,他把刚才落在笔记本上的樟树叶夹进去,当作温州的小纪念。
中巴车驶入温州城区时,街道渐渐热闹起来。路边的商铺大多挂着醒目的招牌,“温州皮鞋”“瓯派服装”“精益眼镜”,还有不少商铺门口摆着模特,穿着最新款的衣服,模特的手腕上挂着“工厂首销”的纸牌。偶尔能看到“小吃店”“海鲜排档”的红色招牌,门口贴着“温州特色”的红纸,有的还摆着玻璃柜,里面放着做好的鱼丸、鱼饼,用保鲜膜盖着,旁边放着试吃的小牙签,店员戴着白色的手套,热情地招呼着路人:“尝尝看,新鲜做的鱼丸,不好吃不要钱!”
五马街是温州的老牌商业街,青石板路被来往的行人踩了几十年,表面光滑得能映出骑楼的影子,石板的缝隙里长着些黄绿色的青苔,在晴天里像撒了把碎翡翠。街道两旁的骑楼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木质的门窗上刻着简单的雕花,有的窗棂上还挂着红灯笼,灯笼上写着老字号的名字——“五味和”的黑底金字招牌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据说这家店光绪年间就有了,现在还在卖温州的传统糕点;“金三益”的招牌是暗红色的,门口摆着几匹布料,店员正拿着软尺给顾客量尺寸;而“老李灯盏糕”的黄色招牌,在一众深色招牌里格外显眼,上面画着个大大的灯盏糕,旁边写着“始于1993年”。
陆帆跟着人流走进五马街,脚踩在青石板上,能感觉到石板的微凉透过鞋底传上来。街道两旁的商铺大多是两层楼,一楼是店面,二楼是住家,有的住家窗户上挂着洗好的衣服,蓝色的床单在风里轻轻晃动,像一面小小的旗帜。路边有卖瓯柑的阿姨,推着个竹编的小推车,车上的瓯柑堆得像座小山,表皮是橙黄色的,带着点青色的斑点,阿姨手里拿着个剥开的瓯柑,吆喝着:“瓯柑哦!甜中带点酸,败火!五块钱一斤,买两斤送半斤!”她的温州话带着软糯的调子,哪怕听不懂,也觉得亲切。
“老李灯盏糕”在五马街的中段,店面不大,只有十几平米,门口搭着个简易的棚子,棚子下面摆着个不锈钢的大油锅,油锅首径有一米多,里面的菜籽油泛着金黄色的光,冒着细小的泡泡,“滋滋”地响着,油香飘得很远,隔着好几家店都能闻到。摊位前围着五六个人,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手里提着菜篮子,应该是买完菜顺便来买的;有背着背包的游客,举着手机在拍;还有两个穿着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踮着脚尖往里面看。
摊主是对中年夫妻,男的负责炸灯盏糕,女的负责收钱、递糕,还有收拾桌子。男摊主大概五十岁左右,头发里掺着些白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件白色的粗布褂子,褂子外面套着个透明的塑料围裙,围裙上溅了些油星,像撒了把碎金子。他手里拿着个特制的铁勺——勺柄很长,有半米多,勺头是圆形的,边缘向上翘着,像个小小的灯盏,这就是做灯盏糕的模具。女摊主比男摊主年轻几岁,头发扎成个低马尾,用黑色的皮筋绑着,穿着件蓝色的碎花围裙,手里拿着个铁夹子,正在把炸好的灯盏糕放在控油的铁丝网上,动作麻利得很。
“小伙子,要吃灯盏糕吗?”女摊主看到陆帆,笑着问,她的眼角有淡淡的细纹,笑起来的时候像两轮小月亮,“我们家有两种口味,传统的萝卜丝肉,还有创新的海鲜味,要不要各来一个尝尝?海鲜味里面有虾仁和鱿鱼,都是早上刚买的新鲜货。”
“好!各来一个!再要一碗鱼丸汤!”陆帆点头,他早就被油香勾得馋了,连肚子都开始“咕咕”叫。
男摊主听到了,抬头冲陆帆笑了笑,然后拿起铁勺,先往勺里舀了一勺面糊。面糊是乳白色的,里面掺着些绿色的葱花和白色的虾米,看起来很细腻。“面糊要磨得细,这样炸出来的外皮才脆,”男摊主边舀面糊边说,他的温州话比女摊主稍重些,但吐字清晰,“我们用的是早稻米,比晚稻米更有韧性,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磨,磨好的面糊要醒半个小时,这样才够筋道,不隔夜——隔夜的面糊发黏,炸出来软趴趴的,不好吃。”
他把铁勺倾斜着,慢慢转了一圈,让面糊均匀地沾在勺壁上,形成一个半厘米厚的“灯盏”形状,勺底留着空,用来放馅料。“转的时候要慢,不然面糊厚薄不均,有的地方炸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男摊主说着,从旁边的瓷盆里舀了一勺馅料——传统口味的馅料是萝卜丝和五花肉,萝卜丝切得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颜色是淡黄色的,撒了点盐和糖,看起来很清爽;五花肉切成薄片,肥瘦相间,像琥珀一样。他把馅料均匀地铺在勺底的面糊上,然后又舀了一勺面糊,盖在馅料上,用勺子轻轻压了压,“这样馅料就不会漏出来了,炸的时候油也不会溅进去。”
接着,他又拿起另一个铁勺,做海鲜味的灯盏糕。海鲜馅的馅料是虾仁和鱿鱼,虾仁是本地的白虾,个头不大,大概有拇指盖那么大,剥了壳,晶莹剔透的;鱿鱼是新鲜的,切成小丁,颜色是淡粉色的,旁边还放着一小碗切碎的葱花和姜末。“海鲜要新鲜,不然有腥味,”男摊主说,“我们每天早上都去南门码头买,那边的渔民刚靠岸,鱼啊虾啊都是活的,买回家自己处理,虾仁要挑去虾线,鱿鱼要撕去外皮,这样吃起来才干净。”
做好两个灯盏糕的生胚,男摊主把铁勺放进油锅里。油锅里的油一下子“滋啦”一声,冒起白色的油烟,油烟裹着油香,瞬间弥漫开来。他用长筷子轻轻扶着铁勺,让灯盏糕在油里慢慢炸,“炸灯盏糕要掌握火候,火太急了,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熟;火太慢了,外面软了不脆,”男摊主说着,用筷子轻轻翻动了一下铁勺,“你看这油泡,小而密,说明火候刚好,大概两分钟就能炸好。”
陆帆站在旁边看着,油锅里的灯盏糕慢慢从乳白色变成淡黄色,再变成金黄色,边缘开始微微发焦,像镀了层金边。男摊主时不时用筷子碰一下灯盏糕的外皮,“硬了就差不多了”,他说着,把铁勺从油锅里捞出来,用筷子轻轻一挑,灯盏糕就从勺里滑出来,落在控油的铁丝网上,油滴从灯盏糕上滴下来,落在油锅里,又发出“滋滋”的声响。
“趁热吃!”女摊主把两个灯盏糕用纸袋包好,递给陆帆,纸袋是牛皮纸做的,上面印着“老李灯盏糕”的字样,还有个小小的灯盏糕图案,“刚炸出来的最香,凉了就软了,不好吃了。”她又转身从旁边的锅里舀了一碗鱼丸汤,放在陆帆面前的小桌子上,“鱼丸汤配灯盏糕,解腻,你尝尝,鱼丸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添加剂。”
陆帆接过纸袋,指尖能感觉到纸袋传来的温度,有点烫手,他忍不住先咬了一口传统口味的灯盏糕。外皮果然很脆,“咔嚓”一声,声音很响,牙齿刚碰到,就有股油香和米香混着萝卜丝的鲜气涌进嘴里——萝卜丝吸满了油,甜中带点咸,还有点嚼劲;五花肉的肥油己经被炸出来了,渗进萝卜丝里,一点都不腻,反而让萝卜丝更鲜;面糊的米香很浓,还带着点葱花和虾米的鲜气,层次很丰富。
他又咬了一口海鲜味的,虾仁很Q弹,咬开能感觉到虾肉的纹理,带着点海水的鲜气;鱿鱼丁很嫩,嚼起来有股独特的鲜味,和面糊的米香混在一起,比传统口味多了一层海洋的味道,却一点都不腥。“好吃!”陆帆忍不住赞叹,“两种口味都好吃,传统的鲜,海鲜的香,各有各的味道!”
“很多老顾客都爱吃传统的,”女摊主笑着坐在陆帆对面的小凳子上,手里拿着块抹布,擦着桌子,“他们说吃的是小时候的味道,比如隔壁的张阿公,每天早上都来买一个,说我们家的灯盏糕和他年轻时吃的一样,没走味。但年轻人喜欢新鲜的,我们就想着加个海鲜味,一开始还担心没人吃,没想到卖得还挺好,现在每天能卖出去几十份海鲜味的——做生意嘛,不能太死板,要跟着市场变,但传统的手艺不能丢,比如面糊的磨制、火候的掌握,这些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变了就不是老李灯盏糕了。”
陆帆喝了一口鱼丸汤,汤是乳白色的,加了点葱花和醋,酸中带鲜,刚好解灯盏糕的油。鱼丸大概有乒乓球那么大,颜色是淡粉色的,咬开里面是鱼肉的纹理,没有鱼刺,很Q弹,鲜得很,比他之前吃的速冻鱼丸好吃太多了。“鱼丸也很好吃!”他说,“里面的鱼肉很实在,没有掺淀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