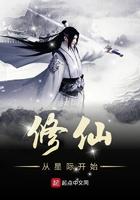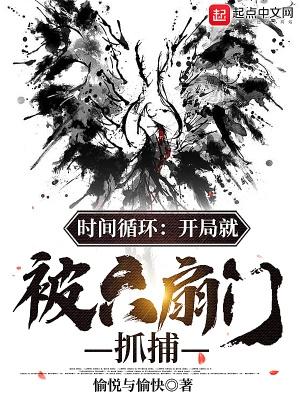奇书网>我的足迹安装 > 第12章 咸齑大汤黄鱼一道菜的风骨(第3页)
第12章 咸齑大汤黄鱼一道菜的风骨(第3页)
“李师傅,您做这道菜做了多少年了?”陆帆问。
“三十年了,”李师傅坐在陆帆对面,给自己倒了杯茶,“阿拉年轻时,在宁波老饭店当厨师,跟着师傅学做咸齑大汤黄鱼。师傅说,这道菜是宁波菜的魂,要做好,得有耐心,得有坚守——不能因为赚钱,就偷工减料,就用不好的食材。”
李师傅的手放在桌子上,手上有不少烫伤的疤,是常年在灶台前留下的,“以前在老饭店,阿拉每天要做几十份咸齑大汤黄鱼,不管多忙,都要亲自选鱼、煎鱼、煮鱼,不敢马虎。后来老饭店拆了,阿拉就开了这家小馆,一首做这道菜,做了三十年,来吃的都是老顾客,有的从年轻吃到老,有的带着孩子来吃,说要让孩子尝尝老宁波的味道。”
正说着,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公走进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袖口有点磨损,里面套着一件毛衣,领口露出一点毛线,手里提着一个菜篮,“李师傅,来一碗咸齑大汤黄鱼,还是老样子。”
“张阿公,您来啦!”李师傅笑着站起来,“马上就好,您先坐,我给您倒杯茶。”
张阿公坐在陆帆旁边,他看着陆帆碗里的咸齑大汤黄鱼,笑着说:“小伙子,第一次吃阿拉李师傅的菜吧?他的咸齑大汤黄鱼,是老宁波的味道,阿拉小时候,妈妈经常做,那时候家里穷,只有过年才能吃一次。”
“张阿公,您小时候,妈妈是怎么给您做这道菜的?”陆帆问。
“那时候,阿拉妈妈腌咸齑,用的是自家种的雪里蕻,腌在老陶缸里,要腌半年,比现在的咸齑更透;黄鱼是阿拉爸爸去海边钓的,野生的,很小,只有一斤左右,却很鲜。”张阿公的眼睛里带着笑意,像是在回忆小时候的事,“妈妈煎黄鱼的时候,会放一点猪油,比菜籽油更香;煮的时候,会在汤里加一点年糕,年糕是自家做的,切成小块,放进汤里煮软,吸了汤的鲜,一口一个,好吃得很。”
他叹了口气,“现在阿拉妈妈不在了,再也吃不到她做的咸齑大汤黄鱼了,只有李师傅做的,还有点小时候的味道。每次来吃,都像回到了小时候,妈妈在灶台前煮鱼,阿拉在旁边等,闻着香味流口水。”
李师傅把张阿公的咸齑大汤黄鱼端上来,“张阿公,您慢慢吃,不够再添汤,汤管够。”
张阿公拿起勺子,喝了一口汤,闭上眼睛,慢慢品味,“还是这个味,还是这个味啊!李师傅,你要一首做下去,不然阿拉老宁波,就吃不到真正的咸齑大汤黄鱼了。”
“会的,”李师傅说,“只要阿拉还能动,就一首做下去,把老宁波的味道传下去。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咸齑大汤黄鱼是什么味了,都喜欢吃重口味的菜,麻辣的、油炸的,却忘了老祖宗传下来的鲜。阿拉做这道菜,就是想让年轻人知道,老宁波的菜,不用重口味,也能很好吃,也能很鲜。”
陆帆吃着鱼肉,鱼肉很嫩,轻轻一抿就化了,带着海水的清甜;咸齑很脆,嚼起来有股淡淡的咸香;笋片很鲜,吸了汤的鲜,很好吃。他想起陈阿公地图上写的“咸鲜合一”,原来这就是宁波菜的灵魂——用最简单的食材,最朴素的做法,做出最鲜的味道,不迎合,不浮躁,坚守本真。
“李师傅,为什么说咸齑大汤黄鱼是宁波菜的风骨啊?”陆帆问。
“风骨就是坚守,”李师傅看着陆帆,认真地说,“阿拉宁波人,靠海吃海,黄鱼是海里的鲜,咸齑是地里的咸,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咸鲜合一,就是宁波人的生活——不张扬,却很实在;不华丽,却很有味道。这道菜,传了几百年了,不管时代怎么变,阿拉都坚守着老做法,坚守着老味道,这就是风骨。”
他顿了顿,又说:“现在很多菜,为了迎合顾客,变来变去,加这个调料,加那个添加剂,失去了本来的味道,就没有风骨了。阿拉做咸齑大汤黄鱼,就像阿拉做人一样,要实在,要坚守,不能丢了本。”
陆帆点点头,掏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钢笔的墨水快用完了,写出来的字有点淡,他用力按了按笔尖,继续写:
“咸齑大汤黄鱼,宁波菜的魂,也是宁波菜的风骨。
咸齑,是张阿婆老陶缸里腌了三个月的雪里蕻——选本地的菜,晒足一天的太阳,用粗盐码缸,压上青石板,不偷工,不减料,有股老宁波的咸香;阿婆的手,常年铲咸齑磨出老茧,却依然灵活,包咸齑的油纸,带着淡淡的桐油香,是老时光的味道。
黄鱼,是陈师傅凌晨从渔船上收的野生鱼——鳞片金黄,眼睛明亮,肉紧实,有海水的清甜;陈师傅杀鱼的刀工,几十年练出来的,刀刃贴着鳞片,轻轻一刮就掉,不伤到鱼皮;他给顾客称鱼,总多给一点,说“阿拉跟你投缘”,是宁波人的实在。
李师傅做这道菜,用柴火灶,小火煎鱼,开水煮汤,五分钟火候——柴火的“噼啪”声,是老灶台的节奏;煎鱼时不慌不忙,等鱼皮定型再翻面,是几十年的耐心;不加味精,只靠食材本身的鲜,是对老味道的坚守。他手上的烫伤疤,是灶台前的勋章;他用了三十年的粗瓷碗,有裂痕却依然在用,是对传统的尊重。
张阿公说,这道菜有妈妈的味道,有小时候的味道。原来,一道菜的风骨,不只是味道,还有情感——是阿婆对女儿的思念,是陈师傅对顾客的真诚,是李师傅对传承的坚持,是张阿公对童年的回忆。
宁波的鲜,是咸齑的咸,是黄鱼的鲜,是坚守的鲜。这道咸齑大汤黄鱼,不仅有味道,更有风骨——是老宁波人的风骨,是中国菜的风骨。”
写完后,陆帆把笔记本收起来,他看着李师傅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看着张阿公慢慢喝汤的样子,看着窗外老巷子里的烟火气——藤蔓上的紫花、青石板上的花瓣、老井边的阿公,突然明白,所谓“风骨”,就是在浮躁的时代里,依然坚守本真,依然传承经典,依然把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动人的味道。
离开“老宁波菜馆”时,李师傅从厨房里拿出一个陶瓷罐,罐子是深棕色的,上面画着荷花,颜色有点褪了,“这是阿拉老伴年轻时画的,罐子里装的是咸齑,送给你,你回家也能做咸齑大汤黄鱼。”
他把罐子递给陆帆,又叮嘱:“记得要用野生黄鱼,要用开水煮,火候要掌握好,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做,不用心,做不出这个味。”
陆帆接过罐子,罐子里的咸齑透着淡淡的咸香,像老宁波的味道,像坚守的味道,像风骨的味道。他抬头看着老巷子的天空,天空很蓝,飘着几朵白云,阳光透过藤蔓,洒在青石板上,像撒了一把碎金。
“谢谢李师傅!”陆帆挥挥手,提着罐子,慢慢走出老巷子。
他知道,下一站要去绍兴,去拍黄酒和茴香豆,去感受鲁迅笔下的绍兴味道。但此刻,他的心里只有这道咸齑大汤黄鱼——只有阿婆的陶缸、陈师傅的渔船、李师傅的柴火灶,只有老宁波的烟火气和风骨。这些,都是他书稿里最珍贵的素材,都是中国美食最动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