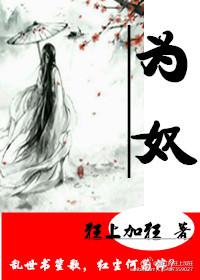奇书网>明末边关将领 > 第163章 征辽铁路(第1页)
第163章 征辽铁路(第1页)
李睿那封“修建征辽大动脉”的奏折,并没有立刻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而是先一步被送到了宁远城内“周氏商行”那座不起眼的宅院里,送到了那位正因后院亲手栽种的几株玉米苗长势喜人而沾沾自喜的“黄老爷”手中。
当崇祯皇帝展开那份措辞激昂、充满了“忠君报国”之情的奏折时,他那张因为享受了几天田园之乐而略显红润的脸,瞬间就凝固了。
“征辽大动脉?”
他看着这几个充满了杀伐之气和宏大叙事感的词汇,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他身旁的王承恩也是一脸的困惑。
“老爷,这李总兵又是唱的哪一出?”他小声地嘀咕道,“前些天京城里的言官才刚刚弹劾他,说他修路是为了‘谋反’。他怎么还变本加厉,直接就要把路修到沉阳城下去了?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崇祯没有说话。他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李睿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他走的每一步都必然经过了精密的计算。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深意。
“走。”
崇祯缓缓地站起身,将那份奏折收入袖中。
“去总兵府。我,要亲自问问他,他这条‘大动脉’,究竟是想输送什么‘血液’。”
总兵府的书房之内,依旧是一炉温酒,两个人。只是这一次,气氛不再象上次那般充满了江湖豪情,而是多了一丝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试探与博弈。
“李兄弟,”崇祯开门见山,将那份奏折放到了桌上,“你这份‘大礼’,可是有些烫手啊。”
“哦?”李睿故作不解,明知故问,“黄大哥此话怎讲?为国修路,直捣黄龙,此乃我辈军人分内之事。何来‘烫手’一说?”
“你我之间,就不必说这些场面话了。”崇祯的眼中闪过一丝锐利,“你很清楚,朝堂之上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你。你此刻抛出这份奏折,无异于是往那早已烧得通红的油锅里,又添了一把干柴。你就不怕那些言官会借此机会,将你彻底打成一个意图不轨的‘国贼’吗?”
“怕?”
李睿笑了。他缓缓地站起身,走到了那副巨大的舆-图前。
“黄大哥,你觉得什么是路?”
他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崇祯一愣,下意识地回答:“路,自然是供人马车辆行走之道。”
“不错。”李睿点了点头,“在绝大多数人眼中,路就是路。”
“所以,”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当我说要修一条路去打鞑子的时候,那些言官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他拿起一支炭笔,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从山海关通往沉阳的弯弯曲曲的虚线。
“他们想的,是我们-要征发数十万民夫,耗费数百万两白银,用上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去开山辟路,修建一条传统的、可以供大军和粮草马车通行的军道。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到时候,他们便有了一万个理由可以来弹劾我,攻讦我。而我,也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他们为我设下的舆论陷阱之中。”
崇祯听得连连点头。他知道李睿说的句句属实,这正是那些文官集团最擅长的党同伐异的手段。
“可是,”李睿的话锋猛地一转,脸上露出了如同狐狸般的狡黠笑容,“他们都错了。因为我说的‘路’,和他们想的‘路’,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