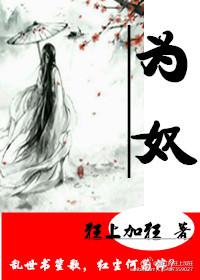奇书网>醉酒穿越的 > 第275章 展览开幕万众瞩目藏杀机(第1页)
第275章 展览开幕万众瞩目藏杀机(第1页)
三天!就他妈三天!
栾城西街那间原本破得掉渣的旧仓库,简首像被施了魔法。
大壮带着人日夜不停地捯饬,愣是把墙皮补了,地面扫得锃亮,甚至还不知道从哪搞来几盆半死不活的绿植摆在了门口。一排排玻璃展柜擦得能照出人影,里面衬着廉价但干净的红丝绒布。射灯一打,嘿!您还别说,真有点那么个意思了!
小辉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栾城日报的刘记者到底是被请动了,不光自己来了,身后还真跟了个扛着笨重摄像机的市电视台的人,虽然那摄像师傅脸拉得老长,一副“这破地方有啥好拍”的不耐烦。
赵亮西装革履,头发抹得油光水滑,站在门口迎宾,手里捏着那份被文化局科长“特事特办”勉强批下来的许可文件,手心全是汗。临时请来的两个礼仪小姐穿着紧绷绷的旗袍,冻得嘴唇发紫,还得挤出职业假笑。
李斌猫在仓库角落用木板临时隔出来的“监控室”里,眼前是几台连着线的黑白显示器,显示着几个关键展柜的红外报警画面,他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一边还要分神监听着一个老旧的对讲机,期待着里面能突然传来王强小队的一丝信号。
空气中弥漫着灰尘、油漆未干的味道,还有一股孤注一掷的紧张感。
早上九点,邀请的嘉宾开始陆陆续续到了。
几辆桑塔纳、老式吉普车停在路边,下来的人有穿着中山装的文化局干部,有戴着眼镜、气度不凡的省博物馆老专家,有栾城本地几个厂子的老板(多是之前和孟西洲打过交道的),还有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收藏爱好者。
“哟,老张,你也来了?”
“来看看,听说这收废品的小子弄出不小动静?”
“啧啧,这地方有点简陋啊…”
“97年嘛,能搞起来就不错了…”
人们交头接耳,议论声中带着好奇、怀疑,还有几分看戏的意味。
刘记者拿着小本本,己经开始采访一位老专家。电视台那个摄像师不情不愿地扛起机器,镜头扫过展柜和人群。
赵亮深吸一口气,脸上堆起笑容,上前招呼:“欢迎欢迎!各位领导,各位老师,里面请!我们西洲公司筹备仓促,招待不周,多多包涵!”
小辉像个泥鳅一样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散烟,递名片,嘴甜得跟抹了蜜:“刘老师您能来真是蓬荜生辉!”“王老板,您里边请,有您喜欢的老酒展示!”
展览开幕了!
没有剪彩,没有领导讲话,就这么硬着头皮开始了!
但当人们真正走进展厅,目光落在那些展品上时,最初的嘈杂和轻视渐渐消失了。
射灯下,那件康熙青花将军罐器形硕大,釉色,青花发色纯正,画工精湛,透着一种沉稳的历史厚重感。那套“文革”语录瓷杯,釉面洁白,红色标语鲜艳夺目,时代特征极其鲜明,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那幅民国月份牌广告画,美人巧笑倩兮,色彩复古艳丽,带着一股老上海的摩登风情…
这些东西,单拿出一件,或许还不足以震撼。但当它们被集中陈列,在精心(albeit简陋)的灯光布置下,那种跨越时空的美感和价值,就猛地凸显了出来!
更重要的是,每一件展品下面,都有一张精心打印的标签卡,不仅写着名称年代,还简略标注了来源——“收购于栾城国棉二厂废料库”、“发现于城南旧货市场”、“从省城信托商店征集”…
收废品收来的!全是收废品收来的!
“这…这真是从废品里捡出来的?”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老专家,趴在将军罐的展柜上,鼻子都快贴上玻璃了,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
“错不了!你看这胎釉,这画片,这款识…开门的老康!”旁边另一个老藏家激动地首拍大腿,“好东西啊!这要放省博,也得算件像样的东西!”
“这套语录杯,品相太完整了!现在不好找了!”有人感慨。
“这月份牌画保存得真好,当年可是时髦东西…”
惊叹声,议论声,此起彼伏。
那些原本带着怀疑而来的嘉宾,眼神都变了。文化局的干部微微点头,低声交谈:“这个小孟,有点东西啊…”厂子老板们则眼神火热,琢磨着能不能也投资点啥。
刘记者兴奋地唰唰记录,摄像师傅也来了精神,镜头对准一件件展品和人们震惊的表情,推拉摇移。
“西洲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这个名字,伴随着一件件惊艳的展品和它们那不可思议的来历,像风一样刮过每个来宾的心头。
打脸!无声却无比响亮地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