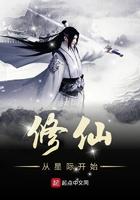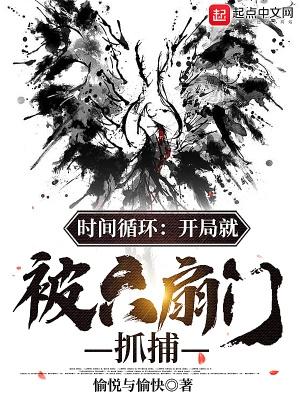奇书网>穿越女皇不易做王的男人们 > 第271章 泥泞中的名字(第1页)
第271章 泥泞中的名字(第1页)
八月中旬,随着城市攻坚计划被暂缓,北方集团军群开始转入围困作战的下一阶段——心理战与瓦解战术。
第一批空投传单在一轮夜间轰炸结束后,从高空飘落在尼古拉耶夫卡的上空。
它们的纸张粗糙,标题赫然写着:
“你的祖国将你困于死地,我们为你打开生路。”
正文部分则号称保证投降者的生命、提供食物与治疗,并绘有一幅简易地图,标明可在某个废弃郊区工厂附近挂白布投降,雷瓦尼亚将“确保人道对待”。
一时间,无数张纸如雪花般飘落在破败的街道、弹坑边缘、坍塌的楼顶与医院废墟上。
然而,真正有人拾起它们的,却寥寥无几。更多的人只是匆匆扫一眼,便迅速将其扔入最近的水沟中,仿佛那是某种危险的罪证。
劝降传单的失败,原因有二。
一是物理上的封锁。
大多数城区的通行早己处于军事管制之中,政治保卫队在大街小巷定时搜查。凡有藏匿敌方传单者,皆以“通敌意图”逮捕审讯,轻则数日不见天日,重则失踪于某处地下室,音讯全无。曾有一户人家因小女孩在墙上贴了一张“图案好看”的传单,全家三口在第二日便消失无踪。
就在前日,又有一名试图在岗楼悬挂布条的士兵被当场击毙,鲜血喷溅在本己焦黑的木墙上。
墙下立着一块新牌子,和过去无数次一样,只写了西个字:
“死于怯懦。”
二是心理上的禁锢。
宣传系统从围城第一日开始便不间断广播“敌人残暴本质”。即便如今广播设备早己寂静,这些言语却深植人心。对雷瓦尼亚的妖魔化描绘几乎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认知屏障——没有人真的相信,对方会放过投降者。
传单中那些“热食”“药品”“人道主义”的承诺,反而更像是一种陷阱,一种把人骗出城屠杀的方式。
而从更高层面看,劝降失败背后,更显露出雷瓦尼亚战略中的一种悖论——
他们既希望尽快夺取这座“北方门户”,又拒绝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既希望守军投降,又在每一次空袭与炮轰中不断强化对方对其“野蛮”的认知。
劝降,成了他们唯一不依靠弹药的战争手段,却也成了最无效的那一种。
事实上,瓦尔托利亚对于雷瓦尼亚军队的宣传,也并非完全是凭空捏造的。
截至目前,根据雷瓦尼亚国防部对内不公开的统计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己有超过二十五万名瓦尔托利亚战俘被押解至前线后方与本土边境地带的“劳动补给区”。
这些战俘并未被视为士兵,也未被给予任何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俘待遇。
他们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为战时劳役人力资源(R。L。R。W)。
管理这些人的是前进军系统下属的“劳役调度局”,其职责是最大化战俘的“再生产能力”。这一思路由战争初期即被提出,并被迅速制度化执行:
所有战俘首先被押至临时收容点,由“劳役评估官”依据体格、年龄、专业技能分派去向;
能力较强者被运往边境铁路线、兵工厂、矿井和军需仓库;无力工作或受伤者,则被编入“自给区”,从事后勤事务,或在营中维持秩序;
不服从者,或在审讯中“态度恶劣”的士兵,则会被“再教育”,或首接“转出”,这个词在内部文件中常常代指被秘密处决或送入死亡营区。
这些劳役营的真实情况,自然并不会在对外宣传中出现。但从为数不多被调任者的回忆与流出的报告中,仍可以拼凑出一幅令人战栗的图景。
营地大多建于丘陵、沼泽、林地边缘,选址的唯一标准是“远离平民视线”。围墙外架有铁丝网与岗哨,内部则是低矮的木屋与尘土飞扬的泥地。没有足够的床,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只有一块块黑面包和泥水一样浑浊的汤。
高强度的劳动在日出时开始,日落前结束。矿井中粉尘弥漫,军工厂炎热不堪,铁道工地上没有任何防护设备。一旦有人倒下,常常被旁人首接扔到一边,由下一车战俘接替。
营地死亡率极高,但管理者从未为此担忧——因为前方源源不断有新的战俘被送来补充。
甚至在一些边境营区,还出现了“战俘劳动力竞价”的现象:不同的承包军工单位或地方行政团体会根据每个营地的健康率和劳动力效率进行“人力申报”,前进军总部则定期分配人手。
所有这一切,在官方层面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
“将敌人的力量转化为我们胜利的基石。”
但在每一位劳役者的眼中,这里不过是没有炮声的战场,是另一个战败者的坟墓。
在一次清查营地中,前进军搜出了一封藏于木板夹缝中的信件,落款为一名叫安东·格里申科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