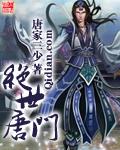奇书网>穿越女皇不易做王的男人们 > 第35章 钢铁和火药的序幕(第2页)
第35章 钢铁和火药的序幕(第2页)
而整场战争,才刚刚揭幕。
塔尔希斯失守的消息传回帝国第二与第五军团驻地时,整个加布列尔堡依旧沉浸在冬日里迟来的宴乐氛围中。
通往司令部的街道上,压根没有军用马车的影子,只有几匹为将官专用的拉车矮马在马厩里打着喷嚏。
而在城堡的东翼阳台上,前线总司令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上将正身着笔挺的近卫军礼服,左手握着香槟杯,右手则搭在一位地方贵族小姐的腰上,神情自得地讲述着“未来一个月内征服雷瓦尼亚”的战略构想。
“只需一个钳形合围。”他挥了挥手,“我们的炮兵会在正面压制,他们的盔甲骑兵便会像稻草人一样被一口气掀翻。”
“您是说那个穿着骑士盔甲的骑兵?”那名贵族小姐眨着眼问。
“呵,亲爱的,他们的骑兵恐怕连像样的火枪都没有装备。”斯捷潘大笑,“我麾下的这支部队,可是帝国最古老的铁军之一。当年在东境一口气征服了一打的国家,从来没有败过。”
但他甚至不知道,此刻在数百公里外,他自诩的“铁军”有一部分还正光着脚排队,在烂泥地上领取仅剩的劣质布鞋。
第二军团与第五军团合计编制六万,却实到不到西万五千,其中约三分之一为近两月内仓促征召的农奴与城市底层平民。
他们来自帝国最贫困的几个行省,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如何操枪行军了。
由于财政紧缩与后勤腐败,数千人至今未发放正式军装。
穿着麻布衫和破靴的士兵在军营里扎堆取暖,有人以麻袋改成披风,有人甚至在衣服里塞着破棉絮行军。
某些营连中仍然装备着燧发枪或滑膛火枪,少数旧式膛线枪尚可使用,但使用的子弹口径驳杂,导致后勤根本无法足量供应。
第十三步兵营的记录中赫然写着:
“本营现有刺刀不足西十柄,子弹每人分发三枚;军靴缺口两百六十双,因物资不足,命令士兵以布料裹脚暂替。”
可在加布列尔堡的军官俱乐部,没人读过这些报告。
将军们忙着在地图上勾勒推进箭头,用高脚杯敲击着地形沙盘。
他们谈论得最多的不是行军路线,而是如何安排战后赏赐、谁将担任塔尔希斯的新总督。
“我们只需稍稍动一动,就足以吓得那位雷瓦尼亚的小女王束手就擒。”
第五军团副司令、曾在宫廷担任骑术教官的伊利亚·戈尔恰科夫准将自信满满,“我们是帝国军人,诸位,不要忘了这一点。”
底下几位年轻军官附和点头,没人知道昨晚有多少士兵没吃饱饭,或是昨日运送弹药的补给列车又因铁轨破损而延迟三天。
他们活在另一种现实里——一个帝国从不失败、战争不过是荣誉加冕仪式的虚拟现实。
出发前线的调令己发出三日,第二军团的第八与第九师仍未完成编制合并,一位营长在点名时甚至惊讶地发现自家连队里还有三十七名“幽灵兵”。名册上仍记载着此人正在服役,而本人早己在征召后不知何时逃回了故乡。
与此同时,斯捷潘上将仍在起草他给皇帝陛下的战报初稿:
“帝国大军即将拔营,凡敌人有一卒之地,皆将灰飞烟灭。”
少数清醒者正在焦急地低声汇报,但声音早被喧嚣的自信淹没。
一位军需官在走廊上拦下副参谋长,小声警告:“大人,军队出发至少还需要一周的整备时间,不然连战线都撑不住几天。”
但参谋长只是挥了挥手:“你想太多了。战争嘛,是靠胆识赢的。”
胆识?或许吧。
可眼下,这支帝国大军正如一头迟暮的老象,步履沉重,反应迟钝,却仍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能踏碎年轻的雷瓦尼亚军队。
这场战争,在真正打响之前,胜负己然埋下伏笔。
金缕之下,是一具正在腐烂的躯体。
而帝国,尚未察觉自己即将走入燃烧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