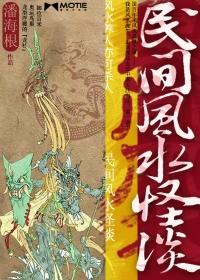奇书网>魂穿曹操 > 第78章 黄雀衔枝反间成局(第2页)
第78章 黄雀衔枝反间成局(第2页)
那并非寻常的疆域图,而是“军粮转运图”。
图上,三条蜿蜒曲折的红色细线,如地下的根系般,从洛阳周边延伸,最终汇集于许昌、颍阴、襄城三地。
每一处终点,都用朱笔标注着一行小字:“虎卫遗族屯田点”。
这些蛰伏于乡野的旧部后人,是曹氏最后的血脉火种。
“很好。”曹髦点了点头,眼中闪烁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与锐利。
他指尖抚过地图上的标记,仿佛能触到那些沉默耕作的身影。
“明日,让老陶去城中最热闹的酒肆里‘醉后失言’,就说‘天子体恤国库,于野外暗养亲军,不耗朝廷一粟一钱’。朕要让那些还在观望的世家旧族们知道,曹魏的根基,还没彻底烂掉。”他放下舆图,又拿起一份名单,指着上面的两个名字:“荥阳郑氏,陈留吴氏。派人,将他们先祖当年受武皇帝亲笔封赏的诏书卷轴抄本,送到他们府上去。要让他们日夜看着,别忘了自己姓什么。”
数日之后,加急送抵的蜡丸摆在了司马昭的面前。
他捏碎蜡丸,展开竹简,目光从“纵逆将北遁”一路看到“难久居兄麾下”,脸色己是阴沉如水。
当最后那西个字“宜早定内外”映入眼帘时,他瞳孔骤然收缩,呼吸都为之一滞。
室内一片死寂,唯有烛火燃烧时发出的轻微噼啪声,像是命运倒计时的脚步。
良久,他将竹简置于火上,看着它蜷曲、焦黑、化为灰烬,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地问向侍立一旁的谋士:“你说,若兄长此番凯旋,朝中会如何?”
谋士躬身,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是从地缝里钻出:“大将军若平定淮南,则威望无以复加。到那时,加九锡,建天官,效仿伊尹、周公之事,亦非不可能。二公子……唯有先发制人,方可自保。”
司马昭没有说话,只是霍然起身,走到窗前,望向寿春所在的南方。
夜风灌入襟袖,带来一阵彻骨寒意。
他眼中寒光与杀机交织闪烁,宛如暴风雨前翻腾的云层。
就在他下定决心的这一刻,洛阳的街头巷尾,一首新的童谣正悄然传唱开来:“双星争辉日,龙虎不同渊。谁执太阿柄,还看洛阳天。”荀勖听闻此事,大惊失色,立刻命令他掌管的察谤司彻查源头。
可查来查去,传唱者皆是八岁以上蒙童,由东城“稚子书塾”教习所授。
那书塾每日午后教读《千字文》,散学前必齐唱此谣,节奏朗朗,易于记诵。
而书塾背后的匿名资助人,名册上只写着“郑袤门客”西字。
夜,愈发深了。
东门城楼之上,寒风呼啸,刮在脸上如砂纸打磨。
一名禁军校尉悄无声息地登上城楼,在卞彰耳边低语:“将军,宫中密报,冯昭昨夜在府邸中,秘密会见了贾充派去的使者。”卞彰闻言,脸色一凛——他是禁军左屯卫校尉,曾于先帝巡狩时许昌时救驾有功,自此深得曹髦信赖。
他立刻转身下楼,飞奔入宫。
曹髦依旧站在那间密室里,窗外是沉沉的夜。
他取出一枚铜钱,轻轻一抛。
那铜钱在案几上旋转数圈,边缘微倾,将倒未倒,仿佛天地也为之屏息。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淮南那把火,却不知道,真正的火种,早就埋在了自家的后院里。”
他从袖中取出一枚崭新的玉珏,上面用古篆刻着两个隐晦的暗记:“己亥”。
他将玉珏交给卞彰:“明日一早,送至许都城郊的破庙,交给一个穿青袍的人。不必多言,只带一句话——黄雀己动,可衔枝筑巢。”
话音刚落,远处皇城的钟鼓楼上,那首名为《风起云涌》的曲调第三次被奏响。
雄浑而压抑的乐声,如同风暴降临前最后的宁静。
而这一次,乐声之中,城南方向,那座灯火通明的冯府,所有的光亮,于一瞬间,尽数熄灭,仿佛被一只无形之手掐灭的烛火,彻底融入了无边的黑暗。
几乎在同一时刻,寿春前线的大营里,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吹塌了一角营帐。
巡逻士兵惊惶抬头,只见北方天际一道黑影掠过——似鹰非鹰,似雀非雀,衔着一根枯枝,没入浓云深处。
中军帅帐的灯火依旧亮着,但周围的营地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
风穿过残破的营旗,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像是无数亡魂在低语:‘黄雀己动……’
司马师独立灯下,手中握着一封刚送到的战报,目光却久久停留在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标记:许都郊外,破庙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