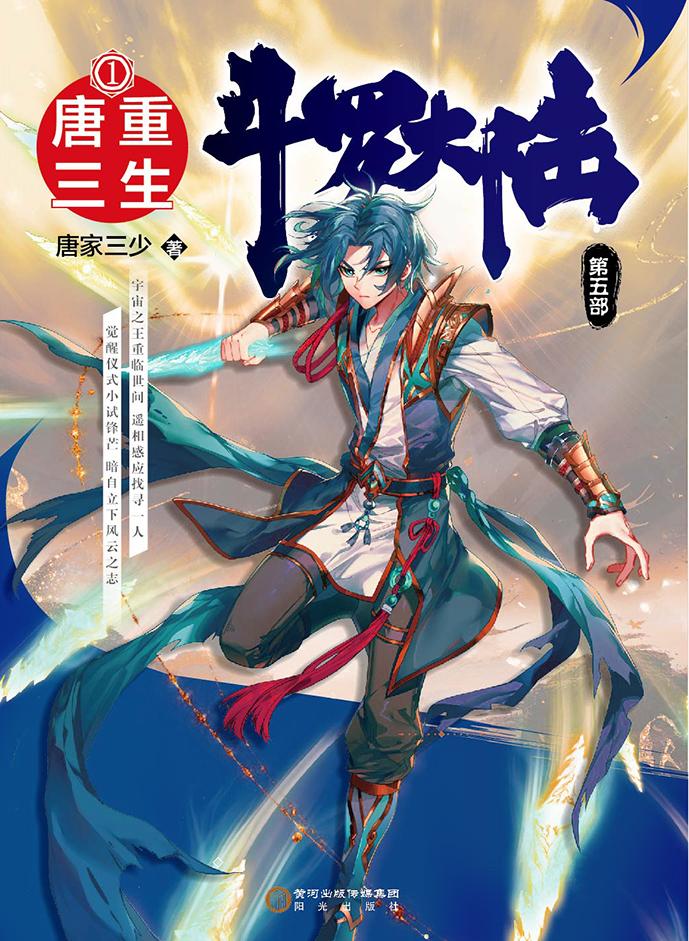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炼金术是什么意思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他还在我身后絮絮叨叨,说一些自以为对严凛的了解,我关上了耳朵,屏蔽他的声音,直到听见他说——
“你真的为了严凛没去日本?”
我这才猛然停下脚步,怒火中烧地回头质问:“我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第二外语学的日语,在几家日资传媒公司实习后收到了他们总部公司的邀请。当时甚至工作签证都快办好了,我才突然反悔说要来美国留学,但这都是我非常私人的事,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他看我有所反应,勾起嘴角,更加吊人胃口地说:“你猜呢?”
“爱说不说。”我作势要走。
“你不觉得自己愚蠢吗?”他试图激怒我。
我反问:“和你有什么关系?”
“呵。”韩骋发出一声讥笑,“那你觉得和严凛有关系吗,你为他放弃大好前程,他多看你一眼了吗?”
“他没有,但我还是那句话,和你到底有他妈的什么关系?”我的耐性几乎快被磨光。
“就是好奇,好奇什么样的人能这么贱。”
我过去没少被人骂过这个字,但基本都是严凛的朋友,而他,还没这个资格。
竭力克制自己的怒火,我佯装平和地问:“好奇完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希望他能一口气问完,而不是时不时来倒人胃口。
他装也不装,干脆道:“你和严凛睡过吗?”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这么一本正经地问出这样直白又无耻的问题,愣了又愣,最后说了句:“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那你们谁是上面的?”他另辟蹊径追问。
我不回答他可以说我是默认,我回答,呃……我该怎么回答?沉默片刻,我一字一句陈述事实:“他不是同性恋。”
韩骋眼神变化莫测,幽深地盯着我说:“那可未必吧?”
看到我脸上一瞬而过的不可置信,他露出得逞的笑,“看来还真不是啊。
,碰面,我没有他新的电话号码,联系只能依靠电邮。
这些信件都石沉大海,一度让我以为他搁置了这个邮箱地址,肆无忌惮地每天碎碎念,俨然把邮件当成了日记本。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猝不及防地收到了自动回复的“rrychristas”,这才知道他还在用,立刻收敛起来,只是偶尔发几封问(骚)候(扰)一下。然而他还是从不回复,不过我也不气馁,乐观地秉持着一贯的我行我素原则,锲而不舍地进行单线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