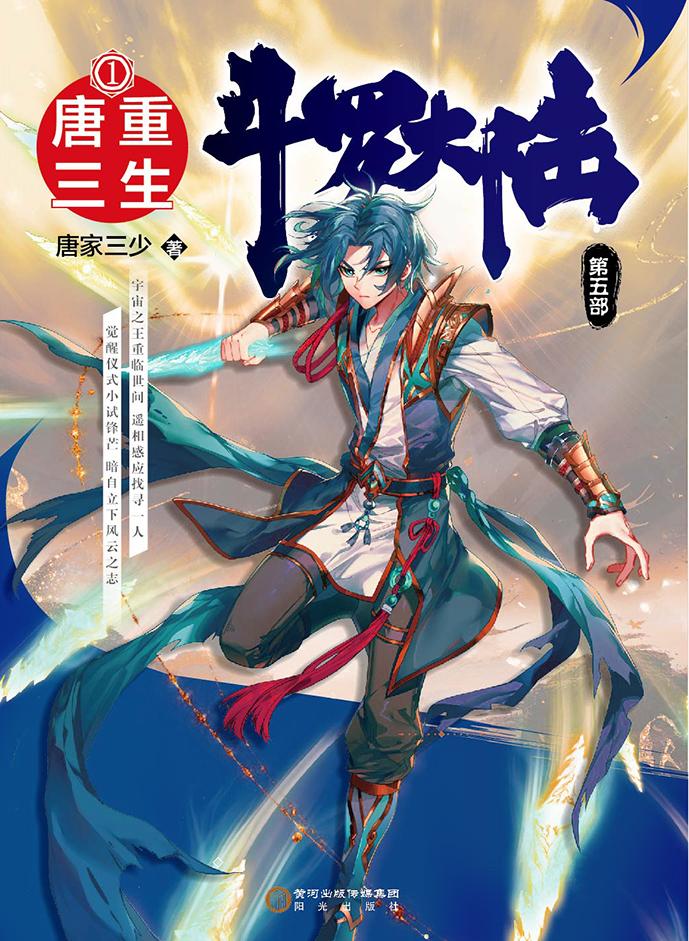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被迫嫁入反派阵营百度 > 第63章(第2页)
第63章(第2页)
沉在如此灯火下,视野因灯火而迷蒙,瞧什么都似裹上层铜镜色,种种思绪此刻沉入底,什么都漫上散不去的温情,陷入那暧昧不堪的氛围里。
谢知珩搁下镊子,放入医药箱里。眸眼的光华在他数次偏头移眸中,流转过多,掀起的种种波澜,也在他缓缓垂落的长睫下,息于平静。
他的声音夹杂了些暗哑,谢知珩低声与晏城说:“郎君怎又去惹陶主簿?”
大理寺两位主簿素来无恩怨,时常可见他们同伴相行于街巷中,有时过于亲昵,都被好事者奏到谢知珩跟前来。
都于主簿位置上享清闲,政见上无分歧,不算政敌,自是哥俩。
可不知为何,两人虽交好过密,彼此间的友谊非是一帆风顺,时常戏耍对方是平常。
今日,却落得大打出手。伤势瞧着不太重,只点点霞粉,好似陶严不是揍人,而是执笔在晏城嘴角处轻扫胭脂。
晏城鼓着脸腮不满,盘腿贴着谢知珩坐:“哪里是又了?我什么时候惹过清肃,就是个玩笑,跟他开个玩笑!”
二人在大理寺中打闹也非罕见,一月不有一次,都得让殷少宿探头怀疑,两人情谊是否有点淡了,或是谁遇上事了。
“即是玩笑,郎君也不可太过戏弄陶主簿,乱你二人友情可不好。”
谢知珩为晏城处理过嘴角伤势,仍觉有些疲累,他俯身靠在晏城肩膀处,散发如绸缎般垂落,覆在晏城新换的月白色衣袍上。
浓茶已遮不住眉心的疲倦,晏城为他揉了揉太阳穴,他不会按摩,只能用这细小的举止,来缓缓始终缠绕谢知珩的梦魇。
偏垂头颅,脸颊相贴,耳廓相压,晏城低声问:“殿试春耕已过,朝野仍这般忙碌吗?”
谢知珩被压着,声音闷闷的:“也不算忙碌,琐事不少,宰相皆能分忧些许。只是……”
他话语没完,晏城随之瞧去,只见书桌上具是奏折。紧急重要的红壳不在,应是在宫中处理过,只余绿壳蓝壳的奏折。
“还有这么多奏折!”晏城大惊。
虽然官品不高,可晏城仍是有上奏的权力,奏折外壳的颜色代表,他仍能分清。
可令晏城崩溃破防的不是堆如山高的奏折,而是堆有三四座的蓝壳奏折,每一份都崭新如初,不曾惹落半点灰尘。
晏城崩溃:“不是,我俸禄都被他们弹飞了,怎么还有这么多!我烧都烧不过来。”
气得脸颊鼓鼓,谢知珩都听见他气愤磨牙的声音,不算突出的虎牙,似要磨灭般。
可生气了,晏城气得想直接唤来宫人,将所有奏折都丢在火坑里,不管是蓝壳还是绿壳,红的也丢进去。
就知道弹劾人,没人弹劾,就盯着他一个人!
怎么他脸上有钱呀,弹一次,俸禄就涨一次吗!还是会官升封爵,一人来弹,他们全家皆会飞升是吧!
好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