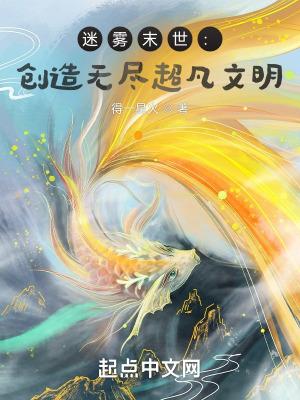奇书网>忆君王珍珠周奉疆 > 3040(第29页)
3040(第29页)
佩芝声称皇后出事时是一人独处室内,周遭并无旁人伺候,宫娥们是在听到皇后呕血的声音时才进去的。
皇帝又问:“那在这之前呢?她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
佩芝垂首,声音也低了些:“别的也没什么异常之处,唯有今日,娘娘还牵挂颍川公主府的冯氏母子,是而召见了冯氏和她那失明的长子,很是心疼她长子韩柏的样子,还厚厚赏了冯氏母子。”
皇帝重重呼出一口气:“那就是冯氏母子在她跟前说了什么了?她受见了那小儿失明的样子,受了惊讶了?”
“这倒也没有。”佩芝回忆了下,十分肯定地对皇帝说,
“冯氏因她儿子的缘故,现在可是老实得不得了,一共也没开口对娘娘说几句话,都是娘娘问什么她才说什么。若说是心疼她儿子,娘娘是有些心疼,可见完冯氏后,娘娘还是好好的,还说去内殿里歇一歇,等会再去太后宫里请安呢。——后来娘娘就是在这时出的事。”
这下连皇帝也没辙了。
他只能命人再细细地查,将这几日接触过媜珠的所有人都再细查一遍,看看到底又是什么缘故。
佩芝安慰皇帝:“陛下别急,等娘娘醒来了,陛下亲自去问问娘娘,娘娘自会对陛下亲口说出的。”
皇帝很疲倦,他只能在心里想,但愿如此吧。
被媜珠吐出的血弄脏的那块狐皮地毯,很快被宫娥们拆卸下去处理了。
不过,在当时,宫娥们取走的也只是被弄脏的那一块,之后找来新的替换上。
所幸是媜珠慌乱之中藏着信纸的那块狐皮并未被弄脏,所以宫娥们为了省事,也没有掀开来仔细查看过。
这时候椒房殿内外依旧免不了人心惶惶,宫人也是人,他们心中畏惧,在主子看不见的地方,难免做事时有些心不在焉,也就免不了有些慌手慌脚。
——而谁也不曾想到的是,这一次他们等着媜珠醒来,居然是在足足十天之后。
在皇帝快要崩溃的最后一刻。
第40章
起先,医官们一再向皇帝保证说皇后并无大碍,只要静养静养,给娘娘施针后再喂服一些汤药,娘娘一定会很快醒来的。
皇帝虽然焦虑,可也只能姑且先信了他们的话,平日里还会照旧赴朝会、处理政务,然后他会将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来陪伴媜珠,守在媜珠的床边,沉默地看着她,等着她醒来。
但是,当三天过去后,媜珠仍然不见丝毫起色,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昏睡在榻上时,皇帝的焦躁之情益盛,怒火也不断飙升,每日都要将那些医官们叫过来斥责数遍不止。
他也不再朝会,而是几乎整日寸步不离地守着媜珠,只有一些最重要最紧急的奏章被送到他面前时,他才会皱着眉头批阅一下。
他心情极差,待下更为严苛,整得宫内宫外人人自危,所有人都夹紧了尾巴屏住了呼吸,唯恐在这时节又惹了皇帝生气。
赵太后也跑过来嚎了两嗓子,一副哭天抹泪的架势:
“我好好的女儿交到你手里,不过三年五载之间,如何就这样大病小痛不断了!当日你又是怎么跟我赌咒发誓保证的,说要一辈子如珠似宝千金万金地对她好……”
周奉疆根本就没心思搭理她。
赵太后觉得没意思,于是抹了抹泪也就走了。
过了几日,她又跑过来哭,这次是哭皇帝不上朝的事。
她当然不是担心臣下们对皇帝这种荒唐的行为有所异议,反正不是她的亲儿子,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和她没什么干系。
只是,她气就气在她觉得皇帝是在咒她。
——国朝仪制,皇太后丧,帝辍朝五日。
太后这个年纪的人,已经自觉将自己视作老人来看待,当然是很忌讳这种事的,她心中越想越不痛快,越想越不高兴,于是又借机找了个由头到皇帝跟前闹一番,皇帝仍旧不理。
这时候他已经在媜珠跟前守了数日了,魂不守舍衣不解带地过了好几日,把他自己也折磨得神容颓唐憔悴,双眸布满赤红的血丝,看上去分外骇人。
恐怕赵太后和他说了些什么,他都没听入耳去。
赵太后撇了撇嘴,又自觉没意思地走了。
然而再过一两日,赵太后又来了。
这一次她是带着满腔的怒火来和皇帝告状的。
她说,这几日因为皇后昏迷不醒,外头有些狼心狗肺的蛇鼠之徒,竟然都打量着窃议皇后是不中用了,还隐隐议论说皇后的身子连今年入春都熬不到,眼看着是已经油尽灯枯了。
这起人各怀鬼心,甚至还欲暗中结成朋党,意欲推举扶持下一位新后入主椒房殿,哪怕选不上新后,也算计着要向皇帝的后宫里送几位昭仪美人。
——这可是一个崭新帝国的皇后之位,只要赵皇后一死,谁能再得到君王的宠幸,哪怕只是以末品更衣入侍,若能第一个生下小皇子,生下皇帝的第一子、本朝立国以来的第一位皇子,那都是一下贵不可及,翻身跃进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