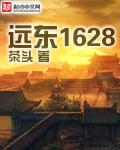奇书网>白玉长茄简介 > 章五(第1页)
章五(第1页)
是夜。空寂宫室内,玉壶独坐于一方木几前,凝神翻阅伯无咎送来的皇后寝宫图纸。身畔琉璃宫灯忽明忽灭,烛火摇曳间,她的倒影与窗外树影在地面交错,恍若鬼影浮动。
此次祀礼皇帝因病留宫,德妃日日侍奉在侧,她的一双儿女皆留于宫中陪伴。伯无咎代皇帝主持郊祀大典,领宗室贵族,文武百官一同随行,浩荡前往道泽行宫。甫至行宫,玉壶便依计划潜入皇后寝宫查探。皇后已逝,寝宫空置已久。只有侍卫值守及宫人例行清扫,伯无咎已事先将值守侍卫打点妥当,玉壶每日趁洒扫宫人离去后潜入,便可安心探寻兵符所在。
然两日过去,玉壶却一无所获。
太尉虽留密信与皇后,提及将兵符置于皇后寝宫,然未言明兵符到底藏于寝宫何处。玉壶自认已费心搜寻,可实在找不见一丝兵符踪迹。
夜色愈发浓重,殿内幽暗,惟有烛影与玉壶相伴。她只手托腮,指尖不自觉抚上额角,心知今日又要无功而返。
殿门被无声推开,感到夜风钻入殿内,才发觉有人前来。那人站在暗处,玉壶一时看不清来人面容。待对方缓步近前,烛火映照下,才认出伯无咎。他托一盏茶水站在她身前,冠帽未解,身上着朱色仪服,袍摆曳地,尚未卸下白日的庄重。
伯无咎代皇帝行事,自抵达行宫,便不得闲暇,每日需主持的祀礼尤其繁重。这还是到行宫后玉壶第一次见他。
灯影明灭,玉壶觉出伯无咎眉宇间的疲色,身形也似清减了些。从来温润的眉目也沾染上他一贯压抑的阴郁,愈发生人勿近。祀礼前后需斋戒,不可沾荤腥,近日又诸事压身,想来伯无咎也未有片刻休整。
伯无咎将茶盏推至玉壶手边,立在她身侧,垂眸看向几上图纸。嗓音有些沙哑,却仍带温和:“偃师查得如何了?”
“殿下恕罪,仍无进展。”玉壶坦言道。
“可有什么难处?”伯无咎神色不改,言语间亦无责备之意。“祀礼不过四日,本宫知晓时日尚短。偃师若有何需要,尽管开口。”
玉壶目光掠过殿内陈设,沉吟片刻,轻声道:“确有一件。”
伯无咎已掀袍坐下,隔案与她相对:“但说无妨。”
“公主殿下提过,召我之前,两位殿下已数次暗中派人搜寻此处,均是一无所获。”
“不错。”
“太尉大人也曾遣人寻过兵符,亦是无果。”
“正是。”
“虽是推测,陛下既不喜郭太尉跋扈,又与太子殿下离心,恐怕也令人寻过这块兵符罢。可即便是皇家工匠,亦无功而返。”
“……”
伯无咎不答,面上已有不愉之色。
“胡玉斗胆,殿下可曾想过,皇后寝宫既无暗室,也并未藏有兵符。”
伯无咎面色一沉,复又克制,勉强舒展眉目,仍冷笑出声:“偃师是说,外公与母后的密信是假,分明是戏弄本宫?”
皇帝抱病一月,伯无咎身为太子,需为君父分忧,纵然宫内局势纷乱,他仍远离京城,亲持郊祀大典。如今宫中是德妃把持,且她的幼子,一向受皇帝宠爱的八皇子也未赴郊祀,反倒留待皇宫。道泽山几日虽短,宫中情形却瞬息万变。他虽面上波澜不惊,想来身在局中,又如何能真正云淡风轻。他于宫中本就处处受制,若此次郊祀未有转机,待他回宫,形势只怕会更加艰险。玉壶想起午后回公主寝殿小睡时,听伯无忧谈及郭太尉今日又借机施压,要太子交出先皇后密信。
玉壶敛下眉目,不再多言。
连续数日诸事压身,伯无咎已有几分烦躁,此时更像是被点中什么,言语间带着不耐:“你既道是承先师遗命,便尽好分内之事,休得胡言。”
说罢便即起身,负气而去。将出殿门时,伯无咎步下微顿,却未再说什么,终是离开。
殿门开阖,夜风再度卷入。玉壶仍坐于几前,面色如常,并不被伯无咎的怒意触动,复低头翻看图纸。良久,她伸手熄灭将尽的烛火,起身离开。
郊祀第三日,夜。
明日过后,郊祀便至尾声,众人届时就要返京。皇后寝宫内灯影摇摇,浮动于空寂宫室,一如前几日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