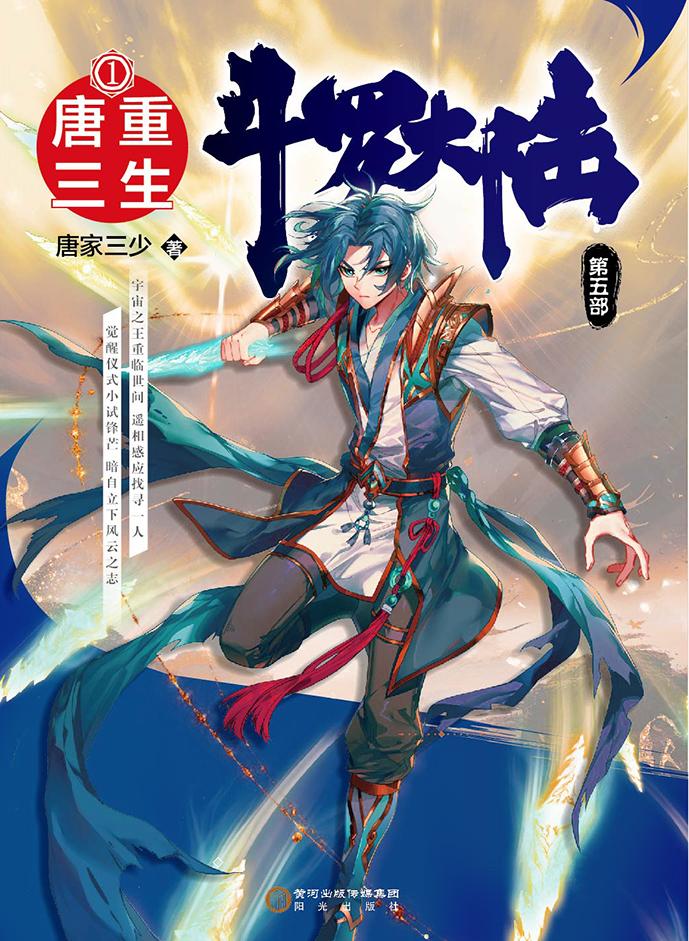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启示录2006百科 > 第46章 娶母中未结婚即戴上绿帽(第5页)
第46章 娶母中未结婚即戴上绿帽(第5页)
我的目光扫过她因紧张而微微起伏的雪乳,掠过那纤细腰肢下的臀线,最后定格在她那双即使此刻也依旧媚意流转的眼睛上,嘴角勾起一抹带着冷意的笑容,问道:
“妈,我问你个问题。”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回避的穿透力,“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当初我没考上交大,也没能通过选调生考试,成不了国家干部,只是一个在上海底层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你,还愿意像现在这样,放弃所有,铁了心要嫁给我吗?”
问题抛出的瞬间,客厅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妈妈江曼殊脸上那娇嗔和愤怒的表情瞬间僵住,她眼神闪烁了一下,下意识地并拢了那双裹在透明丝袜里的**长腿,这个细微的防御性动作,似乎已经暴露了她内心真实的答案。
其实答案早已心照不宣。
我深知,她或许永远都会以她扭曲的方式“爱”我这个儿子,但她的爱,如同藤蔓,需要缠绕在强壮的树干上才能向上攀爬。
这树干,就是钱和权,是稳定优渥的生活保障。
没有这些,她那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爱情”和“奉献”,不过是无根浮萍。
我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抛出更残忍的假设,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要剖开她所有的现实与算计:
“再如果……考上重点大学,成为国家干部,拥有大好前途的人,不是我,而是那个李伟芳。妈,你是不是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他,而把我……像丢垃圾一样抛弃在一边?”
妈妈被我这两个连环的、直击要害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
她丰润的红唇张了张,想说什么辩解的话,但在我那洞悉一切的目光下,任何虚伪的言辞都显得苍白无力。
她沉默了足足有十几秒,保养得宜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睡袍光滑的布料,最终,像是放弃了最后的掩饰,她抬起头,迎上我的目光,眼神里没有了平时的媚态,只剩下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
“是。”她吐出一个清晰而冰冷的字眼。
她顿了顿,仿佛在陈述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生存法则,语气平静得令人心寒:
“维民,妈不想骗你。当初……我答应给王公子做生活秘书,后来……又去招惹韩小针,确实就是为了能攀上高枝,嫁入豪门,让我们母子能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她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如果……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考上大学、前途无量的人是李伟芳,而不是你……妈……妈肯定会想方设法嫁给他。这跟他是谁没关系,只跟他的‘价值’有关系。”
听着她如此赤裸、甚至带着点理直气壮的坦白,我一时竟有些无语。
靠着一个如此“坦诚”地将儿子也纳入价值衡量体系的母亲,我不知道是该感到悲哀,还是该“庆幸”于她的毫不虚伪。
然而,就在这冰冷的现实几乎要将人冻结时,妈妈的话锋却又是一转。
她向前一步,伸出那双曾经抚慰过无数男人、此刻却温柔地捧住我脸颊的手,眼神重新变得**而充满了一种扭曲的占有欲:
“但是,维民,你要明白!”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急切的强调,“无论妈嫁给谁,无论妈躺在谁的床上,妈心里最爱的,永远是你!我的儿子!”她的指尖轻轻划过我的下颌,带着**的暗示,“妈对你的爱,和对其他男人的‘服务’,是两回事!只要你需要,妈随时都可以回到你身边,满足你的一切……需求。妈的身体,妈的心,永远都有你的一份,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份!”
她顿了顿,重新挺直了腰背,那对的几乎要顶到我的胸膛,脸上绽放出一种混合着现实与胜利意味的妖娆笑容,语气也变得斩钉截铁:
“而且,现在说这些‘如果’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实就是——是我儿子苏维民,通过了国家的考验,成了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是我儿子苏维民,有实力、有前途,能给我江曼殊一个风风光光的未来!而不是那个穷酸潦倒的李伟芳!”
她的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仿佛在确认一笔最成功的投资:
“所以,一切假设都不成立!现在,未来,站在你身边,做你妻子的,只能是我,也必须是我!”
她的话语,像是一杯混合了剧毒与蜜糖的鸡尾酒,将最现实的算计与最扭曲的母爱**地搅拌在一起。
我看着她那张美艳绝伦、此刻写满了得意与占有的脸,心中百味杂陈。
我知道,我此生,恐怕都难以彻底摆脱这个既是母亲,又渴望成为我妻子,并且无比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人了。
我冰冷的目光如同手术刀,毫不留情地剖开她试图掩饰的角落,继续追问,语气带着洞悉一切的嘲讽:“那么,那个王公子呢?你口口声声说嫁给我,这里面,又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为了迎合王公子那种喜欢玩弄人妻的变态欲望,把他制定的这场游戏继续玩下去的一环?”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骤然劈开了妈妈江曼殊强装的镇定。
她美艳的脸庞上血色瞬间褪去,那双惯会勾魂摄魄的媚眼猛地睁大,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
她丰满的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沙发背上,仿佛需要支撑。
“你……你怎么会……”她声音颤抖,涂着猩红指甲油的手指下意识地捂住了微张的红唇,“维民……你……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看着她这副惊慌失措的模样,我心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一种冰冷的、验证了猜测的快意。
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毫无温度的笑容,声音平稳却带着巨大的压迫感:
“是的。我知道。我全部都知道。从你们那些肮脏的交易,到他那些见不得光的癖好。”
在我锐利如刀的目光下,妈妈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她颓然地低下头,浓密卷曲的长发遮住了她部分脸颊,却遮不住那份被揭穿后的狼狈。
沉默了几秒,她终于不再狡辩,老老实实地交代,声音带着一丝后怕和无奈:
“是……确实有这么一部分原因在里面……”她抬起眼,眼神复杂地看着我,“那个王公子……他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家破人亡,成了通缉犯……但是,维民,你不了解他们那种人……他们就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总是能找到新的人脉,新的资源,在黑暗中也能织出一张网来……他那种人,就算跌进泥潭里,也不是我们这种升斗小民可以轻易得罪、能够摆脱的……”